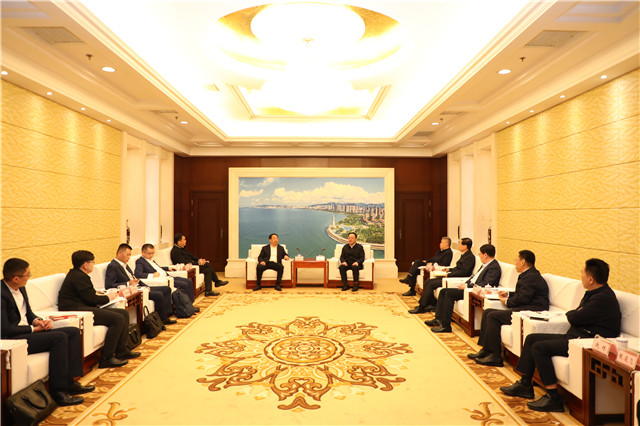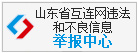抗大胶东支校的日子
刘汉
 刘汉
刘汉(上)
到军政干校去
军校这时已从掖县城搬到掖南山区郭家店附近。郭家店是掖县通往莱阳城的重要集镇,军校驻于郭家店以西的两个村庄,西面靠着马山。这个山区是平(度)、掖(县)边区的大泽山区的一部分,胶东区委当时就住在西边,距军校三五里路。据说当时是想把马山山区建设成一块根据地,这里向南可以深入平度,向东南可以向莱阳发展。但是到了12月,日伪大举进攻胶东内地城市,我们的军队要抗击敌人的进攻,已无暇顾及向莱阳发展。

1939年,刘汉在胶东抗日军政干校。
军校前任校长是丁光。我去后他调回司令部,不久调往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后来被派到太行区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当时军校的前任教育长阮志刚也调走了,他原名袁时若,是威海中学的教员。阮志刚调到《大众报》社任社长,前任政治处主任仲曦东和阮一起调到报社,任副社长(仲曦东原是“三军”四路政治部主任,曾是济南高中的学生)。
和我一起派到军校任教育长的是高锐。他原来是莱阳乡村师范的学生,抗战以后到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毕业后回到山东,这时又派到胶东。他带来延安抗大一整套制度、教材、工作作风等,我们就是依靠这些来办学的。军校政治处副主任宋桂生升任政治处主任,他原是小学教员、莱阳地下党员。这时的军政教员只有一两个人。我去后正在了解情况,还没有正式开展工作。中共胶东区委决定移驻黄县城,要军校也随着去,并通知我带几个人先到黄县县城去看房子。我带着军校供给处两个人随中共胶东区委的大卡车去了黄县。
军校移驻黄县城
我到达黄县后,找到胶东区委王文同志和宣传部长林一山。他们告诉我,区委决定军校改由区委和五支队双重领导,由林一山兼任校长。军校的任务也兼训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并指定军校驻到县城的孔庙里,归胶东区委领导(五支队当时不在黄县)。
不久,军校全体人员由高锐和宋桂生同志率领,经过行军也到达黄县。孔庙里大部分房子是空的,只有大殿里还有不少泥像。我们进驻后,就把大殿改造成一个礼堂。
约在1939年1月,胶东区委根据当时紧张的形势,决定将胶东公学(简称“胶公”)与军校合并。胶东公学是属于专员公署领导的一个民间中学,1938年下半年创办,学生有三四百人,多是黄县人。“胶公”的校长赵野民原是威海中学的教员,和阮志刚一起参加革命。胶东区委考虑,敌人的进攻将转移到山区,这样的民间中学不适于战斗环境,所以要他们合并到军事性质的胶东军校来。对于原来“胶公”的学生,胶东区委决定尽量动员他们参加军校,实在不愿意干的就劝其退学,教员也是如此。由于“胶公”的领导没有对学生进行积极动员,而军校派去“胶公”商量接收校舍、校产的同志态度又比较生硬,加上学生中有些坏分子一鼓动,说军校要吞并“胶公”,结果学生大部分散掉,只动员到几十个人参加了军校。事后,我和赵野民都受到胶东区委的批评。后来,胶东地区又办起一个“胶东公学”,还是由赵野民任校长。

1939年元旦,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由掖县迁至胶东公学校园。2月,胶东公学在撤离途中与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胶公学生大部分转到军政学校学习。
和“胶公”合并的最大收益是合并过来不少教员,这时军校的教员数量是最多的。这期间,军事和政治教员有下列同志:杨介人,军事教员,曾经当过吴佩孚军队警卫营长,同北伐军作过战。“三军”二路起义后,他参加革命。因为他是一个旧军人,二路整编时,部队觉得不便给他分配工作,就把他派到军校来。经过后来工作锻炼和考验,我们觉得此人虽是旧军人出身,但没有兵痞流氓习气,很有训练工作经验,也有战争经验,所以他后来成为军校中的军事教学骨干。
裴宗澄,军事教员,抗战以前在国民党掖县公安局当巡官,后来参加掖县我军“三支队”。“三支队”改编为六十二团时,他曾任营长。后来部队缩编(撤出蓬、黄、掖后,部队有很大减员),他在三四月间被派到军校当军事教员,九十月间又被调回当营长。

1944年胶东公学毕业证明书
刘云鹏,军事教员,曾在抗大学习,后从延安回到山东工作。因为是诸城人,他坚持要求到胶东工作。领导上虽然答应他的要求,但考虑到他曾在国民党军队刘珍年部(曾驻烟台)当过军官,所以没有派他到部队去,而是分配他到军校教书。刘云鹏是继高锐之后来军校工作的又一个抗大毕业的干部,他也带来许多教材和歌曲,并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延安和抗大的新闻。丛鹤丹,济南高中的学生,参加过“民先”,原来在“三军”四路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后来调到军校当政治教员。
还有几个人是从“胶东公学”合并过来的:
王卓青,原是我在济南师范时的英文教员,抗战以后来到掖县他妻子家里,参加掖县“三支队”,后分配到“胶东公学”当教员。
林雅琴(女),王卓青的爱人,原是小学教员。
张秀珩(女),五支队宣传科长罗竹风的爱人,大学生,黄县人,原是黄县中学教员。
迟健民,大学生,和罗竹风都曾在青州当过中学教员。迟是蓬莱人,参加了“三军”二路。二路整编后,他被分配到“胶公”工作,因为腿脚有残疾(腿瘸),身体情况不适宜随军活动,故于1939年秋冬季调出军校。1940年前后,地方又办起一些中学,他被调到蓬(莱)黄(县)联中工作,在1942年“大扫荡”中牺牲。
李绍颜,大学生,黄县人,原是黄县中学的教员。虽然是地主家庭出身,但表现挺好。
这几个人到军校以后都当了政治教员,因为军校没有文化课。赵野民没有合并过来,他留在专员行署工作。当时军校的这些教员,除裴宗澄以外,好像都不是党员。
约在1939年2月,伪军刘桂棠占领掖县县城,紧接着又向黄县县城发起进攻。这时县城里只有胶东区委、专署和少数武装,再就是军校。此时,专员曹漫之负责全面部署城防工作,军校也归他指挥。军校当时只有大约二三十支步枪,还搞来一些土枪土炮。听说掖县失守以前,敌人派来许多特务混入城内,所以黄县曾搞过一次紧急戒严、清查人口,县城人家很多,军校全体出动参加清查工作。敌人进入黄县境内之后,专署布置了撤退工作,让我们组织一个小分队担任部分掩护工作,并准备实行“焦土政策”。我们领来几桶火油,准备烧掉划分给我们的几条街道。在撤退的当天早晨,军校大队由高锐率领,随胶东区委和专署机关撤退,并组成一个土炮队做掩护。另外将持步枪的学员组成一个排由我带领,根据专署发出的命令开始点火,大火只烧光了我们驻扎的黄县中学。当火烧到民房时,老百姓就出来给扑灭了。此时城外的枪声响起,我们奉命撤退。
开始转移到蓬、黄南部的山区。不久,蓬莱城也失守。军校跟随胶东区委连续行军,向南经过招远进入莱阳。专署留在蓬、黄一带组成了北海指挥部,由曹漫之主持,继续坚持该区的斗争。招远那时候被国民党顽固派徐淑明的部队盘踞,我们就驻扎在招远莱阳边境的北泊村(在莱阳城西北,距招远不足十里路)。胶东区委驻在北泊村以北一二里路的张格庄,《大众报》社驻在北泊村以东二里路的石庙村。以后五支队机关也到这一带来了,驻在张格庄以北一二里路的山后村。
当时胶东我军所据有的三个完整县和县城都已失守,机关从城市搬到山沟,有些思想动摇分子逃跑了,部队有较大减员,军校学员中也有个别逃跑的。这次从蓬、黄、掖的撤退,是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一次严峻考验。
(中)
在莱阳北泊村时期
在莱阳北泊村时期
军校从1939年二三月到九十月间,一直驻扎在北泊村,时间较长,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日寇虽然利用刘桂棠占领我们几座县城,但他暂时还不能分兵控制广大乡村,也无力进行“扫荡”。刘桂棠除进攻我蓬、黄、掖三县以外,还攻占了国民党军队盘踞的招远、栖霞、莱阳三座县城。这些国民党顽固派在敌伪的进攻之下,不得不请求我军的帮助。当时曾成立“胶东抗日联军”,却推举由汉奸“反正”的赵保原任联军司令。在所谓的“联合作战”中,我军在黄(县)招(远)一带给刘匪以沉重打击,又单独攻克栖霞城和莱阳城,国民党军队却按兵不动。刘桂棠在我军打击下,向鲁南狼狈逃窜,在逃命途中,他又突然宣布“反正”,成为国民党的“师长”。我军攻克的两座县城都交给了国民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招(远)莱(阳)边区得到一段时间的“稳定”。
在这期间,又有两个刚加入到五支队,一是从国民党鲁东行署拉过来的六十五团,该部队原为我党党员和一些进步人士在胶县、高密一带发动的武装,于1938年底至1939年初开到黄县编入我军,但不久其第一营又叛变投敌。另一部队是我军七、八支队,被山东分局调往鲁南时,有一个团不愿去,回到胶东,经批准被编为五支队的六十四团。不久,这些部队都被整编,连同胶东原来的部队(六十一团已调鲁南)一共只编成两个团(十三团和十五团)。部队虽然缩编,但充实了连队,战斗力反而提高了。以后又成立十四团,是个小团编制。
此时军校与五支队的联系不密切,主要由胶东区委直接指挥。胶东区委对外称“后方司令部”,设有军事部,管理地方武装工作,也负责胶东区委、报社和军校机关的军事指挥。我自从离开掖县城至1939年春,很少回五支队政治部。有一次见到高锦纯,我向他报告军校到黄县以后及撤出的情况,并说明林一山兼任校长的情况。他当时表示不以为然,说胶东区委讨论军校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可也并不是要把军校变成地方性质的学校。他因为不便把领导层的争议向下边讲,所以就没再说什么。
军校因为受胶东区委领导,所以经常参加胶东区委的一些会议,听一些报告。1939年春,我在胶东区委的会议上曾见到于洪锦,这时他已担任北海地委(或工委)书记,和曹漫之一起工作。我当时觉得他的职务提升得很快,但也没有打听他的工作情况。不久,胶东军队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调到上级部门,有的去延安,说是参加“七大”;有的到上级学习;有的去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工作;还有的因历史问题到上级去接受审查等。当时先后走的人有吕志恒(又名吕其恩)、宋澄、宋竹庭、于眉、郑耀南、张加洛、丁光等。于洪锦也去延安了。1945年,我在东北安东市见到吕志恒,他告诉我于洪锦在延安整风时被隔离审查,其间病逝。
军校内部组织到北泊以后已经比较完备,主要是从学员中调出一些人做机关工作或担任学员大队的干部。校部有政治处,下设组织股、宣传股和锄奸股,各股都有两三个干事。组织股长起初是屈夫,屈不久因肺病逝世,继任者是王直夫。宣传股长是宫大非(现改名宫达非),他和王直夫于1939年夏秋之际调往山东纵队的干部学校。锄奸股长好像是丁剑萍。校部的供给处负责物资供应厂的工作,处长叫迟骥。学校的军政教员都归教育长领导。校部还有个卫生所,所长张燕。校部有两个秘书,一个叫孙觉(后来曾接替迟骥担任过供给处长),一个叫孙烈焰(后来改名孙列岩)。
军校的学员分别来自部队和地方,后者占多数。当时我们还在《大众报》上刊登广告招生。1939年初,向军校介绍学员的手续不够严格,各团司政机关和各县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都可以直接向军校介绍学员。后来手续逐渐正规,部队的学员都统一由五支队政治部组织科调来;地方的学员都由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后方司令部或青救会、妇救会的总会统一介绍,但也还是不够严格。

1939年,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第三校(胶东)毕业证。
学员主要是一些小知识分子,入校后即编为大队(连)。每期一两个大队,三四个月为一期即毕业,有时未毕业的学员也往往调出分配工作。毕业的学员都统一颁发油印的《毕业证书》,证书是照抗大的格式印制的。毕业的学员多数分到部队工作,少量从事地方工作。到部队工作的,都由学校介绍到五支队政治部组织科;到地方工作的,则介绍到胶东区委组织部。我也记不清我在校时一共训练了几期学员,因为各个大队毕业的时间不一致,所以大队的数目有时多有时少,一般保持三五个大队在校。大队以下分中队,中队以下设班,大队设大队长、政治委员,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都是学校分派的干部(也是从毕业学员中抽调的),班长由指定学员担任。女生人数较少,一般是编为一个中队或一个班,附属于某一大队,但干部配备较多些。学校还曾专设过民运大队,专门训练地方工作干部。所有学员都穿军装,入校即视同入伍。这一时期,从文登、荣成、牟平一带(后来这一地区称为东海区)曾陆续有许多人到军校学习。此时该区已无我军活动,完全被国民党军队控制。但我党我军在这一带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所以经过我军驻该地区的办事处(曾驻于文登县葛家集)或地方党组织的介绍,有许多青年跑来参军。他们一般都由我地方交通员带领,开始还是成群结队地公开走,后来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拦截,就分散成少数人夜间行动。这些学员在学校一般都表现较好,当时部队中也有这样的反映,喜欢要东海地区的战士。
学员大队的干部经常调换。我记得有刘岩、黄仲哲、宋锡候、冯尚贤、赵恕、王素之、杨西萍、原野、李次哲等。在女生队(班)工作的有徐林、徐平、张青松、张励(原名史点水)等。
当时学校的教育也是按照延安抗大的做法,以政治教育为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传到胶东后,都列为专门课程进行教育。此外着重讲《政治常识》和《中国革命问题》,这两门课程也有从延安带来的小册子作为教材。军事教育有《游击战术》和武器使用、构造等,还有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当时军事教育完全由高锐负责,政治教育则由我多管一些。我也直接讲课,毛主席著作课多由我、高锐和宋桂生同志担任。除了我们自己讲课以外,还请胶东区委的一些领导干部作报告,林一山常来讲政治形势,还请一些同志讲“群众工作”“工作方法”等。
在担任教学工作中,逼着自己非读书不可。为了备课,我找到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籍,生吞活剥地读过,但至多只是懂得其字面的意义,根本不能联系实际斗争,也不知道如何联系。那时的学习态度就是为了增加知识,完全是教条主义的。至于我和各个教员对学员讲课,也是自由主义的,各人自己备课,没有集体研究,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讲,也没有检查、总结和研究如何改进。
学员只凭听课和记笔记,没有统一印发教材,有些教材印发过,也不能做到人手一册。课后讨论都由大队、中队政工干部主持,主要是复习性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只在下次讲课中附带讲讲,很少专门解答。有些学员文化水平很低,只能跟着听讲,课余就自学文化。上课大都是在村外树林中,席地而坐。

帮助群众清洁院内、街道卫生
当时按照胶东区委的指示,在军校中大量发展党员。有些学员入校两三个月即可被吸收入党,主要是抗战坚决、能起模范作用、能吃苦耐劳就可以。当时入党的手续很不完备,一般只一个介绍人,也没有规定候补期,但都是个别吸收,都填写《入党志愿书》,并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在学员大队中,大队政委兼任党支部书记,负责进行党的工作。在校部,由政治处领导这项工作,政治处组织股负责这方面的业务。党员调走时都开具介绍关系的证明信,但当时因战争环境转递不便,都是由本人携带。1939年上半年党的组织还不公开,但也进行一些党的活动,如开小组会、上党课、党员汇报、发展党员等。支部大会一般很少开,党课主要由宋桂生同志负责讲《党的建设》。因为要进行这些党的活动,所以谁是党员在学员中也就很清楚了。到1939年下半年,党的组织就公开了,入党手续也较过去完备,已经开始规定要有候补期。原来入党手续不完备的党员,约在1940年到1941年,根据山东分局的规定,都进行过“完备手续”的工作,需要增加介绍人和规定候补期的,也都按规定办理了。在1939年春季,学校中还有“民先”活动,什么时候停止的已经记不得了,后来才改成“朱德青年队”。
当时在党的干部中就分发和阅读一些党内文件,有山东分局的,有胶东区委的,大部分是工作总结性质或讲解形势与任务的,当时还看不到中央的文件。约在1939年,胶东区委开始出版发行党内刊物《斗争生活》(起初是油印)。
吸收教员入党比在学员中发展党员更慎重一些,因教员多数家庭出身不好,有的人历史复杂,而且他们不像学员那样有“集体生活”以便于考验,所以在教员中发展党员大致在1939年夏秋季才开始。他们当中除了迟健民外,都陆续吸收入党了。张秀珩于军校到达北泊不久就调走了,所以她没有在军校入党。这些教员入党,多数是由宋桂生、高锐和我做的介绍人。
学校的各大队和校部都有“救亡室”的组织,就是俱乐部。“救亡室”常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并出刊墙报。校部的“救亡室”也组织干部和教员唱一些革命歌曲,有时还组织演戏。我记得曾经从旧杂志上找到一份苏联的剧本,由我把人物、情节修改成抗日战争中的故事,组织教员上演过一次。我自己也参加演出,当一个没有台词的“跑龙套”的角色。我和教员们都参与写稿子,刊在“救亡室”的墙报上。
这时《大众报》仍出铅印版。阮志刚同志常约我写稿子,我曾写过两篇政论性的文章,记得其中有一篇是批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此外,军校当时在《大众报》上还辟有一个《军校生活》副刊,出过好几期,主要是宣传军校学习的情况,以号召和影响知识青年。我和几位教员常写一些小文章。我和丛鹤丹还参加过《大众报》上一场关于《牛》的争论,我们都写过反驳和批判文章。
约在七八月,我去国民党张金铭部买枪。军校武器很少,除以前的二三十支步枪外,学员只分发到一些手榴弹,再就是土枪土炮。从黄县撤退以后,学员都不愿使用土枪,保管也不好,损坏了一部分,此时急需装备一批新武器。林一山有一次告诉我,他曾经见到张金铭(林当时参加“抗日联军”的活动),张部能自己制造步枪。他表示愿意卖一部分给我们,要我们派人去和他协商,林一山要我去一趟。这时张与我们的关系还好,我们派了一批政工干部在他那里工作。我带一名警卫员(由锄奸科干部高选担任),骑着马由北泊出发,经过莱西西部,傍晚到达张金铭的司令部(平度东部的祝沟)。次日见到张金铭,我们谈了枪的价钱、取枪的手续。当时他吹嘘他们的枪质量如何好、他们从青岛拉出若干军工技术人员等等,并拿出他们自制的步枪给我看,我们最终谈妥了购买的数目,大约100支。他知道我在军校工作,就请我给他的教导队讲话,我去讲了一次,讲的内容已记不清了。张的政治部里有我们派去的一位刘光耀(女)同志,曾在军校学习过。他们还邀请我去参加一次座谈会,属于联欢性质,我在会上讲了话。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就回来了,之后取枪的事交由学校供给处办理,我再没有去过。
到了九十月间,胶东形势又有新变化。在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赵保原开始对我制造“摩擦”,借口掖县是属于他那个“专员区”的,他是专员,要接收掖县。并且在北泊、张格庄附近炫耀武力,要驱逐我们。这时胶东区委、五支队的机关就向北转移至掖县、招远边境一带,军校也随之转移,从此结束了稳定的教学生活。
(下)
在掖县、招远边区的游击活动
1939年冬季,军校就在掖招边区活动,那里距掖县、招远的敌人据点都只有二三十里路,故不能在一地长时间逗留。这个时期,军校又直接接受五支队的指挥,因为在军事行动上要由司令部统一部署。为了缩小机关的目标,五支队要军校单独活动,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武器,又领到我们兵工厂自制的一批翻造子弹(以硝酸棉作火药),所以能够做到自卫。每次活动,支队司令部都指定一个地区。在敌情较缓和时,也向五支队、胶东区委靠拢,敌情紧张时就恢复单独行动。有一次敌人扫荡掖招边区,军校曾奉命单独插到蓬莱南部活动了几天,有时也到掖(县)北平原地区游击一下。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在掖招边区北至灵山、南至郭家店这一线活动,较常住的村庄是掖县的上庄等地。
为了适应这种游击活动,我们当时很注意掌握附近敌人据点的情况变化。我根据地内经常活动的地区,设有固定的电话线路,几乎走到哪里都可以架通电话和支队司令部取得联系。而且电话站也就是情报站,他们也负责向沿线有电话的单位报告情况。除了利用电话之外,军校单独建立一个侦察班,直属校部领导,调集约8名学员任侦察员,撒向有敌情的区域,做较远距离的警戒。他们主要是依靠我部队和群众中的侦察网收集情况。侦察班对军校的行动安全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侦察班长叫郝滔,侦察员有一个叫刘玉莱,他们都是穿便衣、携带短枪。
学校的军事行动和游击活动方面,主要由高锐和杨介人负责指挥和组织行军、宿营、警戒等。当时军校没有战斗任务,只是保证在游击活动中继续教学,所以这期间并没有发生战斗,也无损失、伤亡。在行军、宿营的空隙时间,还是照常上课。
约在1939年十、十一月间,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参谋长王彬到胶东检查工作。王彬以后就留在胶东,任第三军区司令员,管地方武装的工作(军区是由胶东区委的军事部扩大而成)。黎玉曾到军校讲过一次话,记得是讲工作作风问题,他批评胶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部多,有国民党的“异党情调”。约在12月,黎玉回鲁南,当时有一批军校学员随黎玉去鲁南。向山东纵队输送知识分子也是胶东的一个任务,在这以前也去过几批。山东纵队那时也有个军政干校,驻在沂水岸堤村,所以我们在胶东也知道有个“岸堤干校”,它后来与抗大一分校合并。

迟浩田将军题赠刘汉将军
1940年一二月间,掖招边区还有几次小规模的“扫荡”。3月就接到通知说,抗大要派一批干部到胶东来,当时大家非常兴奋。我在军校这一年多期间,和干部、学员团结得都较好,在生活和工作上也注意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学校的领导干部、教员都和大家吃一样的伙食,一样的行军走路,干部基本上都没有行李。当时军队禁止谈恋爱,不论干部、学员都是如此,这都是从延安抗大作风学来的,对学员的培养教育有一定的作用。但我那时政治上还很幼稚,工作上没有经验,教员的情况也都和我差不多,所以还是按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一套办学。对于改造学员思想、改造世界观等,还没有这个觉悟。虽然对学员进行一些党的政策的教育,但由于自己的政策水平就很低,政策宣传中的片面性必然是很大的。对于这一批知识分子教员,从阶级立场上彻底改造他们也做得很差。从工作作风来说,那时也不知道深入连队,深入群众,只知道去讲讲课、听听汇报而已。总之,这一年多以来,还是摸索着,在“干”中学习吧。
军校与抗大一分校一大队合并以后
1940年4月,军校驻招远的灵山一带,迎来一批胶东的抗大干部,这部分干部原属抗大—分校(山东分校)一大队。他们到校后,就和军校合并成为抗大一分校第三支校,通常也称为“抗大胶东支校”。当时上级决定,由我任校长,廖海光任政委,贾若瑜任副校长。这时在部队中抽调大批学员,编为三个营。我和廖、贾等曾经参加过由王文同志主持召开的一次军政委员会(这是当时一个地区的最高领导组织),会上确定抗大胶东支校只训军队(五支队和第三军区)的干部,不再训练地方干部。领导关系则是既受胶东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又受抗大山东分校的领导。会上对于原来的军校干部各方面都争着要,大体上是分别调给胶东区委、五支队和第三军区。这时五支队司令由刚从鲁南与抗大干部一起到胶东的吴克华担任,高锦纯改任政委。
原军校干部高锐留在抗大支校任营长;宋桂生调到胶东区委党校任校长;胶东区委党校与《大众报》社的机关在1939年12月反“扫荡”中与敌遭遇,党校校长李辰之同志和报社社长阮志刚同志都牺牲了;王卓青也调到党校,后来在1942年(或1943年)宋桂生同志病逝后,继任胶东党校校长;杨介人调任第三军区作战科长;刘云鹏调任五支队作战科长;丛鹤丹好像调到《大众报》社;李绍颜仍留在抗大,任校部秘书。
5月初,抗大胶东支校刚举行开学典礼,还邀请五支队的宣传队准备演戏,获悉敌人已开始“扫荡”,于是连夜转移。这次在胶东是首次规模较大的“扫荡”,持续一个多月。抗大胶东支校刚成立,就投入紧张的反“扫荡”斗争。因学员很多,武器很少(抗大干部来胶东时带了一部分枪支,但不多),所以疏散了一些有病的学员和一些女生,并把武器分配给一些从部队调来的学员,这些学员集中编在一两个连里。这时抗大完全是单独行动,活动地区大体上还是在平(度)招莱掖边区。
约在6月的一天,抗大胶东支校在大泽山区的铁夼寺山沟隐蔽,敌军一二百人突然窜来。当时由廖海光和贾若瑜指挥,派出一个排在北部山口阻击敌人,掩护大队上山。当时掩护部队约有一个班的战士壮烈牺牲,学校大队全部爬上南面的高山。敌人进入山沟后,向山上打了几枪,又放火烧铁夼寺,之后便匆匆跑掉。我们在山上看着敌人的行动,晚上才转移出去。事后,我们派学员掩埋了牺牲同志的遗体。

抗战时期的刘汉夫妇(1942年)
这时赵保原配合日寇夹击我军。有一次我们行军到莱阳、平度边境的姚沟附近,得悉赵保原部向我推进,正好前面有五支队的主力,将投降派赵保原的军队击退,取得一次不小的胜利。这一次抗大支校没有参加战斗。约于7月间,反“扫荡”结束,抗大胶东支校才正式开始上课。我心里很明白,任命我为抗大胶东支校校长是照顾地方干部的性质。虽然从鲁南来的干部对我也很尊重,但我自觉应抱着学习的态度,向抗大干部(尤其是其中的7位红军时代的干部)学习,从他们身上学习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实际工作中,我自己较少发表意见,完全尊重廖、贾二位同志的意见。我热心地阅读着他们带来的一些抗大的教学文件,如教育计划、工作总结和教材等,又虚心地看他们怎样工作,感觉他们对于军校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有一套很完整的办法和经验。再回顾当初我们办军校时的情况,就看出差距来了,这才称得上是“正规教学”。在这一时期,集体备课、集体研究、听课制度、互相检查和互相学习等规矩都不断得到改进与加强。抗大胶东支校成立以后的这三四个月,对于我来说,等于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随着形势的发展,学校的教学体制、教学人员和教学内容都不断地得到充实与完善。抗大胶东支校先后为胶东部队培养了5000余名干部,这些学员把所学到的军事和政治知识,特别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带回到部队,大大提高了胶东地区八路军部队的整体素质。

1946年8月,在胶东公学师范部的基础上成立胶东师范学校。图为1948年胶东师范复校时总务处旧址。
在抗大胶东支校工作时,和我一起工作的领导干部有政委廖海光、副校长贾若瑜、政治处组织股长严政、宣传股长罗义淮、军事教育股长黄径琛、政治教育股长李书厢,营长王奎先、官俊亭、李宏茂、茹夫一,政治教员孙殿甲(还有一些军事、政治教员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政治教导员周澍、吴泰宇等,这些同志都是原来抗大一分校一大队的干部。8月,我奉命调回五支队任宣传科长,结束了在军校将近两年的工作和生活。
刘汉(1916—2008),男,原名刘慕藩,山东省文登县(现威海市文登区)文城人。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宣传科干事、科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校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胶东支校校长、山东纵队第五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胶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山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政治部秘书长、东北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总政治部宣传部正兵团职顾问。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来源:中共威海市委党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