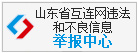文 / 刘致福
茶壶口应该是“叉河口”的变音,位于村南两河交汇处。时间长了村里人约定俗成喊成了“茶壶口”,真名反倒没人记得了。
两条河一条是村南的大河,东西方向,河道开阔,平时水流很浅,河床是洁白的细沙,只在夏季雨后水流才漫过河床。

另一条是顺南山流淌下来的一条小河,南北方向。源头在南山深处,很窄,上游是鳞峋的山石,河水从山上淌下来,漫过山石,冲出很多河坑沙湾。
大概是山水冷凉的缘故,坑湾中鱼虾很多,但都长不大,最大的也只有小手指大小。鱼儿捞上来,放在太阳下晒一会儿便化了。下游相对平坦、宽阔,河床是金黄的细沙。
曾经有淘金汉子在那里挖沙淘洗,被村里人赶走了。村里人忌讳,认为挖了小河,会破了村里的风水。

两条河在茶壶口交汇,冲出一个月牙状的河湾。河湾看似和河床一样平缓,实际靠近沙洲的边缘有一人多深。河湾里鱼很多,而且有大鱼,村南德爷家小儿子,号称“浪里白条”的老三就在里边抓过一斤多沉的鲫鱼。
靠近沙洲的边缘,水草丰美,河岸周围的土被水冲蚀淘空,只余下树根草根,形成很多水洞,成为鱼和螃蟹的栖居地。河蟹又大又肥,老三曾经一个晌午摸过小半桶。
从东北回来的堂兄建平常带我和表弟等几个小伙伴过来洗澡捉鱼。一次大雨过后,大水已经泄了,河面水只有没膝深,表弟不小心走到河沿儿处,扑通一声掉进去,转眼就没影儿了,吓得我们几个哇哇大叫。

恰好德爷家老三从下游上来,一个猛子扎下去,提着表弟的头发拖上来。几个人一起拉到岸上,老三又把表弟肚皮朝下扛到肩上,原地上下跳跃,直到表弟“哇一一”地一声吐出一大口水,老三将他从肩上放下来,看他睁开眼睛,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日积月累,沙洲不断扩大,形成一片望不见边际的林子。林子里植被茂密,以杨树为主,间杂河柳、国槐、榆树,还有棉槐、菠萝等灌木。
地面沙土地上长满了茅草、灯心草、蒲公英、接骨草,都长不高,与杨树等乔木和棉槐等灌木间形成梯次布局,错落有致。冬天树叶全落了,从村里向南望去,只看到乌梢梢的一片林子。
到了春天,林子里一片生机,到处都是花香,有野桃花、梨花、山菊花、金银花。除了野花,地上还有很多宝贝。谷雨刚过,茅草的芽儿便长出针状儿的尖草芽,老家人称为“茅箭”,外壳绿中泛红,用手轻轻一提便抽揠出来。
剥开外壳,里边是雪白的花絮状草花,送到嘴里,绵柔清爽,湿润甘甜。草地上还有一种菌菇,村里大人喊作麻黄杆。
不仅是美食,而且清肝润肺。麻黄杆一支香烟大小,下部是白嫩的细杆,上面是褐色的花帽,似乎是草原上肉苁蓉的袖诊版,从根部掐下来,回家加点虾酱和鸡蛋蒸熟,口感细软,回味清香,是春天难得的美味。
天暖和了,林子便成了小动物的世界。小到沙鳖、蝈蝈,大到草獾、野兔、野狸,还有刺猬、土拔鼠、麻蛇。
最好玩的是沙鳖,只有黄豆粒大小,灰色的甲壳,对细沙情有独钟,一刻也不肯离开。抓到一只,放到平坦的沙地上,眼瞅着它刷刷刷一会工夫便萎出一个漏斗状的沙窝儿。掏出来再放到平整的沙土上,还是如此。
循环往复,没有穷止。兔子夏天很难看到,秋后特别是冬天雪后,才是捕捉的最好时机。林子被雪盖住,聪明的猎人搭眼便能找到兔窝儿。
冬天兔子猫在雪窝里,因为呼吸,雪窝外必会有一个被热气融蚀的圆圈,那下边便是兔窝无疑了。雪停了,兔子外出找食物去了,猎人拿出用竹片做成的夹子,架在雪窝儿门口。里边再放几粒烤过的玉米。
躲到远处树后藏起来,过不了多久便会听到兔子唧唧的叫声,这时紧随猎人的土狗,不用猎人招呼,一个箭步扑过去,叼起兔子交给主人。有时也会惊起别处雪窝儿的兔子,土狗便会紧追不舍。林子雪地上腾起一片雪雾。
树叶长出来,林子就成了鸟儿的天堂。天刚一放亮,鸟儿们便在林子里唧唧喳喳地欢唱。野鸡、斑鸠、布谷鸟、灰喜鹊,还有各种叫不上名来的小鸟。进到林子耳朵里全是各种鸟鸣。
最小的一种鸟儿叫秋叶,只有一片杏树叶大小。浑身葱绿,身子轻盈,精灵般在树枝间跳越。声音细柔,如丝如弦,引得孩子们着迷地追着跑。
从一棵树追到另一棵树,转眼间便不见了,刚要离开,它却啾啾叫着从树叶间飞出来,落到另一片树叶上。飞来飞去,神秘无常,惹得孩子们如痴如狂。
林子里常住的是麻雀和灰喜鹊。灰喜鹊的巢建在高大挺拔的杨树顶端。几百根树枝搭建的鹊巢,是鸟界的高楼大厦。两只喜鹊喳喳叫着,用嘴叼来树枝,一根一根地垒搭,那种功夫、那种执着、那种辛苦,绝不亚于人类搭建楼房。
那是喜鹊夫妻的高层别墅。春暖花开,喜鹊开始孵蛋。好奇的建平趁小夫妻不在,爬上树顶,从鹊巢中取出两只青绿的鹊蛋,刚要装进口袋,喜鹊夫妇喳喳叫着飞回来。
见到偷蛋的建平,嘎嘎狂叫着飞扑过来,吓得建平赶忙顺着树干向下溜,一手还托着两枚鹊蛋。两只喜鹊轮番攻击,挥翅扑打、用嘴叼啄,疼得建平一撒手,扑通一声掉落地上,好在下边是沙土地,没有摔伤,但两只鹊蛋却叭叭跌碎在地上。
两只喜鹊眼见自己的孩子摔成了黄汤,气急败坏地嘎嘎叫着猛扑向建平。建平吓得爬起来抱头就往林外跑,喜鹊在后边拼命地追赶。建平一口气跑到家里,脸上头上已是鲜血淋淋。
喜鹊追到建平家门口,站在他家门楼上嘎嘎叫个不停。这之后几天,建平都不敢出门,只要一露头,喜鹊就会扑过来击打叼啄。一直持续半月有余,再不见建平出来,两只喜鹊才悻悻地飞走了。不知小夫妻后来去了哪里,林子里再沒见到他们的身影。
沙洲的对面是一片芦苇荡。芦苇长势茁壮密集,手指粗的苇杆,足有二米多高。秋冬季节,苇子熟了,孩子们会模仿电影《沙家浜》中的新四军,在芦苇间追逐打闹。
有时不经意间会捡到一窝青绿的野鸭蛋,引得全村的孩子们都往芦苇荡里跑。热闹几天后,芦苇荡重又归于静寂。我和表弟带了吃食和画书钻到里边。
芦苇结实密集,仰身一躺,身下倒下厚厚的一层弹性十足的芦苇,比家里的土炕要舒服多少倍。翻完了画书,吃完了东西,两个人又玩起了迷藏。玩累了,便躺在芦苇大床上看天上的白云,看飞来飞去的鸟儿,不自觉间睡着了。
一天不见人影儿,母亲和哥姐四处喊叫寻找。猛地被喊声惊醒,睁开眼天已经黑了,周围一片漆黑,密密匝匝的芦苇像一堵一堵的墙,怎么也找不见来时的路。
表弟吓得呜呜大哭,惊起几只野鸭,嘎嘎叫着扑愣愣地飞走了。我也头皮发麻,强打精神拉着表弟,循着野鸭飞的方向跌跌撞撞往外走,总算找到了出口。跑回村口,正碰上到处寻找的母亲和大姨,母亲一把拉住我就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埋怨我跑哪儿野去了,一天也不见影儿。
母亲拉我的手抖得厉害。回到家拉开锅盖端出留给我的饭菜,只说了一句:“饿坏了吧,快吃了睡去!”竟没有骂我。
最后一次去茶壶口的记忆令人心痛。那年冬天,雪后的早晨,天很冷。村南德爷早起到林子里拣柴拾粪,刚进林子眼便直了,眼前一棵歪脖树上吊着一个穿戴齐整的汉子。德爷并不认识,德爷吓得嗷嗷叫着往村里跑。后来县里公安来了,全村人都来到林子边上围观。
都不认识,不知汉子是哪里来的,不知什么原因吊在这里。人已经冻成了冰,被公安的吉普车拉走了。人们都散了,林子又空了,但那个人似乎一直吊在那里。

那之后,村里孩子们都不敢靠近林子。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茶壶口。
那之后,我和小伙伴们似乎都长大了。(图/宫举卫)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