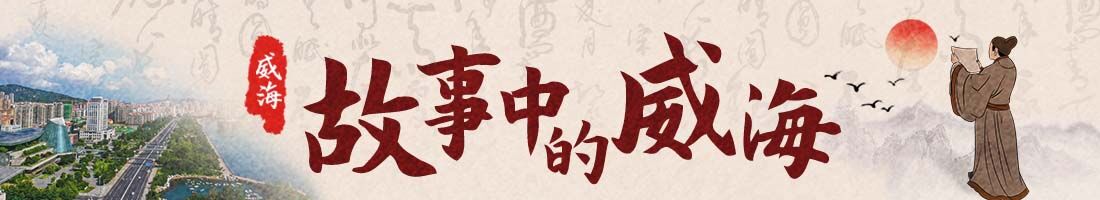
文登县设置于568年,已有1450多年的历史,为文登教育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县学的主要任务是以儒家思想教化百姓,为国家培养并输送人才,即以国家力量办学、督学,让区域子弟就近读书,使教育事业得到发展。

据记载,文登县学宫最早是北宋庆历年间敕建的。
宋以前,文登的教育就已经相当发达。当时政府规定,一县之中,只有读书的超过200人,才允许县办学校,而文登的读书人早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在建县学之前就远远超过这个规模。文登教育的发展如此之早,说明当时文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比较发达的。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发起第一次兴学运动,施行州县立学和改革科举制度,“自此,州郡无不有学”。至宋神宗变法时期,兴学高潮第二次掀起,明确提出普遍设立专职的地方学校、教授和教官,并给学田十顷办学。宋徽宗绍圣年间,由蔡京主持发动了第三次兴学,其声势和规模都超过前两次,地方学校空前兴盛,学校规模空前扩大。这个期间的文登教育体系就已经非常完备。
文登在宋代庆历年间第一次兴学运动中就建有县学学宫,校址在文登县城东南隅,到宋徽宗大观年初修复的时候又增大扩建。此时的文登学宫宏达宽敞,在当时的登州府各县中名列第一,“大观初复增大之,规模宏敞,为诸邑冠”。文登县学能按年向中央国子监输送贡士。
到了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文登县学转向注重教养学生的六德、六行、六艺,宾兴之法等方式,教学体系基本形成,官学的兴办已经名扬四海。
金太宗天会九年(1131),东部沿海几百里爆发反抗伪齐刘豫的农民暴动。第二年,暴动队伍攻陷文登城,文登学宫没能幸免于难,校舍被战火焚毁,设施化为灰烬。战乱过后,文登县学只剩地基和一堆乱石。周边老农在废弃的地基内开菜园,种植蔬菜。此情此景,过往行人无不扼惋叹息。
在此后40多年里,文登县官换了好几任,但县学学宫始终没有得到恢复。每年祭奠先师先圣和祭祀孔子的时候,由于没有祭祀的地点,只能临时在县衙的办事大厅布置祭堂进行。这种有祖无堂,有学无宫,就好比借台唱戏,望山祭祀。此后历经多年,许多任县官在此问题上都不作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学校只得分散上课,小规模发展。尽管如此,仍有人才涌现,仍有进士、举人登上榜贴。官员们只是例行公事,坐享其成。
直到金大定九年(1169),李大成任县令时,情况有了改变。李大成,山东聊城人,任文登县令期间,为政成绩卓然、断案顺理,言行一致,得到文登百姓的拥戴。他初到文登时,对祭孔无祠,入学无堂的现象非常痛心,因而感叹道:“为学者有愧于人,我本人是秀才出身,应该为教育负起责任,不能对此熟视无睹。我们儒家先师孔圣人连个祭祀祭奠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应该感到羞愧。”
李大成决定在县署东面,找一处高而敞亮之地建造学堂。他拿出自己的俸禄,召集能工巧匠,买上好之木为材,采坚硬之石为基,凿石为柱,绳木栋梁。他的行为感动了乡绅,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和帮助李大成早日完成大业。学宫从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开始修建,到大定十二年(1172)完成,历时两年。
重建后的文登学宫,殿、堂、门、庭院、台阶、两厢,依次排列,建筑齐全,房屋高耸。大成殿内,孔子身着闪亮辉煌的衮服,诸位先贤的画像列于两边墙上,整个殿堂庙貌一新、焕然争丽。新的文登学宫又重新巍然矗立在文登大地。
此后经朝代更迭,文登学宫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过多次重修。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文登学宫曾重修过。
明洪武三年(1370),山西顺成人张凤任知县,他和县丞范子贞重修过学宫。
明宣宗宣德年间(1426—1435),知县刘勖等官员组织过重修。明天顺年间(1457—1464),知县李敬、知县孙泰相继重修。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由按察司佥事聂瀛提议,登州推官李淑和、宁海同知谭良诚、文登知县辛三畏共同倡议重修。
嘉靖四十三年(1564)初,知县辛三畏具体负责重修工作,他通过募捐善款,节财谨用,发动民众,身体力行,终于在当年使文登学宫的重修工程得以顺利竣工。竣工后的文登学宫“圣殿辉映,廊庑整饬,启圣有祠,敬一有亭,名宦乡贤,各有祀所”。辛三畏的贡献还在于,“惩颓废,肃学规,因旧为新”。
这次重修的动作较大,建成了棂星门,开辟了云路街,一条大街从学宫直达南城门。据光绪版《文登县志》记载,时任登州刑部主事张栩在《重修碑记》中说,在此次重修前,文登的读书人比李大成重修时增多了不止3倍,且读书风气也盛况空前。
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知县李需光在学宫前建造了“君子能由是路”坊。至此,文登县学的布局完整地呈现于人们面前。县学的最南边是“君子能由是路”坊,坊之北为棂星门,棂星门北为泮池,泮池北为大成门,大成门北为大成殿,大成殿东西为两庑,大成殿之后为明伦堂,明伦堂的东西为进德、修业两斋,棂星门左右为东、西儒学门。东儒学门北为崇圣祠,教谕署在其后;西儒学门北为忠义孝弟祠,训导署在其后。
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知县武光祖;清圣祖康熙十一年(1672),知县邵沆;三十七年,知县朱应文;五十四年,知县张文炳;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知县王一夔;十一年,知县王维干;清高宗乾隆四十七年(1782),知县何燧;五十九年,知县倪企望;清仁宗嘉庆二十年(1815),知县董锡龄;清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知县欧文;清德宗光绪五年,知县彭元照、苏杰等文登父母官都相继对学宫进行了重修。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康熙庚戌年(1670)邵沆来文登赴任后,有感于孔庙的被废弛,上任的第二年春天就提出要重修学宫。看到众人为难,邵沆便提出“上不累国,下不病民”,拿出自己的俸禄,向社会倡导捐助。于是士绅、士人竞相捐献,用了几个月就竣工了。文登学宫又一次焕然一新。
邵沆重修后又过了26年,县学又处于“上雨旁风、鸟栖鼠窜、覆瓦参差、椽柱腐败”的状况,时任知县朱应文,在国库空虚,又不忍心搜刮于百姓的情况下,毅然拿出自己的俸禄率先倡导,士绅响应,历数月而重修完毕,使学宫重新“金壁照耀”。
至明清两朝,文登县学的教育制度日臻完善,各级各类学校健全齐备,学生人数和普及程度都超过了前代。科举制度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士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大有人在,科举成为士人做官的最重要、最为公平的通道。
明清时期,除了县学文登还有乡村十一大区社学、四大书院、六处私立社学,还有营卫四大义学,为士人和百姓子弟求学、求功名提供了较完善的条件。教育设施、教育管理、教学内容都井然有序;童试、乡试都按部就班。没有考取功名的学子,大多承担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工作。这些教官的任职资格主要是举人和贡生,另有虽没考取进士或举人的副榜,也因成绩好被派到县学任教。
元明以来,学署皆有学田,以赡养师生。文登县学的学田本来是很多的,清末还有949亩。这些地,有知县朱应文捐俸买的267亩,知县何燧募捐买的268亩。这样,办学就有了师资经费的可靠保障。为了激励学生学习,学校还通过管理和考试来调动师生积极性。规定文登县学教谕在9年任期内,所教的学生中有3人中举、岁贡和生员各有1人者为合格,达不到规定数额,教师就要降级。廪生10年无成,罚为吏役,退还伙食费。一年中进行月考、季考、岁考、科考四次考试,考后分六等,一等的补为廪生,二等的补为增生,三等不赏不罚,四等鞭打,五等降级为附生,六等取消学籍返乡为民。是廪生和增生的把降下来的空位让给一、二等,原附生不合格降为青衣。这套考试激励措施是非常得力、非常见效的。
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文登县学中,共考中进士102名,举人近200人,贡生660人。清顺治十二年殿试,文登出现“一榜七进士”的盛况,一时轰动京城。他们是于涟、刘䜣、刘煇、于可讬、李曰桂、于鹏翰、丛大为。其中,于涟、于可讬、于鹏翰三人同出自文登大水泊于氏文化家族,于鹏翰与于涟是父子俩,可谓“父子同榜”;刘䜣、刘煇出自文登著名的“十二支刘”的刘氏文化家族,二人是亲叔弟俩,可谓“兄弟同榜”。
康熙五十六年(1717),文登刘重选与堂弟刘重殷、丛荀三人一榜中举,被称为一榜三举人。这些都在当地被传为千古佳话。
(陈强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