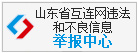编者按:由我市作家唐明华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乳娘》主要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共胶东区委在牟海县(今乳山市)组建胶东育儿所,先后有300多位乳娘(保育员)哺育1223名革命后代的故事。她们视乳儿为己出,冒着生命危险哺育革命后代,讴歌了乳娘群体在峥嵘岁月所展现出来的军民一家、血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奉献精神。今天起,威海新闻网将对《乳娘》进行连载,扫描文末二维码,还可通过有声书等方式全方位了解乳娘事迹,敬请关注!
序幕
1941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困的阶段。
由于战事频发、部队辗转,诸多将士子女难以得到照料,中共胶东区委指示区妇女抗日救国会筹办一个战时育儿所。是年11月,苏政前往荣成县岳家村,依托胶东医院开展工作。此时,苏政已身怀六甲。1942年1月,苏政产下一名男婴。于是,这个起名“东海”的小家伙就成为育儿所接收的第一个孩子。若干年后,苏政在《我离开育儿所前后的情况说明》中这样写道:那时环境很恶劣,产后六天敌人出动。事务长给我做了担架,抬着行军,第八天路上,东海掉下了脐带。
没过多久,因为形势恶化,育儿所转移至荣成沟曹家村,1942年初夏,又转移至乳山县(时称牟海县)的东凤凰崖村。7月,中共胶东区委决定在胶东医院育儿所的基础上,筹建一个独立的胶东育儿所。说是育儿所,实际上,何所之有啊!且不说山村民居蓬门荜户,仅有立锥之地,即便村民腾出房屋,孩子们集中在一起也不易隐蔽。为安全起见,育儿所迁址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周围村庄物色思想和身体均符合要求的奶妈,体检合格后,让乳儿随其在家中居住。育儿所的工作人员不定时地去各户查看。由此,一个传奇故事悄然开篇,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挺身而出,迎着滚滚烽烟走进特定的时代情境。直面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她们不避水火,毁家纾难,先后抚养了1223名革命者的子女,而且这些孩子在日军“扫荡”和多次迁徙中无一伤亡。这些看似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用滴血的乳汁连缀起荡气回肠的国家记忆,成就了世界战争史上的生命传奇。追溯昔日场景,人们看到,女娲补天的全新演绎是如此震撼,人性之花的傲然绽放是如此壮美……
第一章 大爱如天
(小序)
1942年初冬,东凤凰崖村肖国英的第二个孩子尚未满月就不幸夭折了。哀痛之际,村妇救会主任矫凤珍送来了出生只有12天的小远落。她告诉肖国英,远落是八路军的骨血。抱起瘦骨伶仃的小家伙,肖国英心疼地说:“孩啊,从今往后,俺就是你的亲娘了。”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奶水,全家人把仅有的一点口粮全都省给了肖国英。一次,不到两岁的女儿饿得直嚷:“妈,我饿,饿呀,给我吃一口吧。”肖国英看了看仅剩的那点口粮,又看看孱弱的小远落,狠了狠心,抹着眼泪背过身去。
就在肖国英悉心哺育小远落的同时,姜家村的王志兰也在为抚养小冬妮辛苦忙碌。小丫头刚送来的时候,王志兰的儿子只有几个月大,家人提醒她认真考虑一下,但她想都没想就爽快地答应了。由于奶水不足,她生生给儿子断了奶。丈夫怜子心切,埋怨她说:“你咋这么狠心,对待亲生的儿子就像后妈。”她回答说:“组织上既然叫咱拾养(方言,抚养的意思)冬妮,咱就一定得好好待她。自己的孩子怎么都行,小冬妮要是有啥闪失,咱良心上过不去啊!”
为了给小丫头增加营养,王志兰把家里仅有的一只母鸡下的蛋细心攒着;偶尔吃个苹果,皮是儿子的,瓤是冬妮的;尽管家里穷得叮当响,她还是变着法地用玉米面和鸡蛋做成香喷喷的疙瘩汤,每到这时,她就会给丈夫使个眼色,于是,那个可怜的小男孩就被糊里糊涂地抱出去了……
冬妮5岁时被亲生父母接走了,孩子的离去几乎把王志兰的心掏空了。因为思念过度、积郁成疾,两年后,这位年仅38岁的乳娘不幸去世。
滴血的乳汁
命运的敲门声是在1942年那个冬日突然响起的。
从中午起,纷纷扬扬的雪花就开始飘落,直到天色擦黑才渐渐停歇。此时,雪野寂寂,寒气森森,一弯冷月把空气冻得硬邦邦的。
杨家老宅内,晚饭已经端上了炕桌。姜玉英刚抄起筷子,手忽然在空中停住了。好像……西屋后窗响了两下,不会是有人敲窗户吧?姜玉英扭头瞭了一眼,脸上显出些许惶惑。短暂的沉寂过后,敲击声又清晰地传过来——“砰砰”,力道加大,显得有些急迫。男人抻着脖子朝那边喊了一嗓子:“谁呀?”“我,矫凤珍,快开门吧!”姜玉英翻身下炕,趿上鞋,嘀咕着:“这大冷的天,有啥要紧的事啊。”不一会儿,村妇救会主任矫凤珍揽着襁褓急火火地进来了。看到一家人不解的神色,她开门见山地对姜玉英的丈夫说:“坤璞啊,有件事想求你家玉英帮个忙。”说着,朝怀里努努嘴,“这个小嫚是八路军的孩子,爹妈都在前线打鬼子,顾不上,托付咱村给她找个奶妈……”男人的表情有些木讷,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姜玉英轻轻撩开襁褓边脚,只见婴儿皱巴巴的小脸蛋显得有些苍白,两条稀疏的眉毛求助似的彼此靠拢,把眉心挤出一个扭曲的疙瘩。“多大了?”她关切地问。“差两天三个月。”“叫啥名字?”“仙儿。”姜玉英牙疼似的哼了一声:“这么小就离开爹妈,真是怪可怜的。”矫凤珍认真地盯着姜玉英:“组织上找人是有要求的,人品要好,还得利索,不能邋遢。村里合计来合计去,觉得找你最合适。一是你家二嫚已经六个多月了,你现在还有奶水;二是你们的为人大伙都了解,村里信得过。”姜玉英心里一震,最后这句话太关键,也太重要了,就像一簇火星划过堆积在心底的干草,转瞬间,惊喜的火苗开始摇曳。是啊,有生以来,哪里受过这样的抬举呢!不过,兴奋的同时,她的心里也生出几分忐忑。原因很简单,这是八路军的娃娃,容不得半点闪失啊。然而,母爱偏偏具有感性色彩。所以,在选择航向的一刹那,理智的罗盘往往不起作用,而感情和本能在支配一切。她下意识地抬起胳膊,刚要伸出双手,动作却突然凝滞了。她扭转脸,眼巴巴地望着丈夫……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女人必须恪守的规矩嘛!想当初,母亲一边流着泪,一边咬着牙,狠狠地把“三从四德”勒进她的裹脚布里。在凄厉的哭声中,一双秀气的小脚丫拧成了锥形,像纺锤。疼痛过去了,能够下地了,她扶着炕沿,趔趔趄趄迈开步子,那摇摇晃晃的身影愀然暗示:这辈子,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家长和男人的附属品。后来的经历证明,既然没有独立人格,那么,无论大事小事,又怎能奢望自己做主呢?
姜玉英是乳山县(时称牟海县)蓬家夼村人,家中姊妹三个,她排行老二。十八岁那年,她出落得高挑了。看上去,比要好的几个姑娘高出一截,模样虽然说不上多好看,但走起路来,碎步款款,犹如风摆杨柳,颇有几分妩媚。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媒人像采花的蜜蜂一样“嗡嗡嘤嘤”上门了。头几个,父亲都觉得不称心,接下来,却对一个准备续弦的后生有了兴趣。媒人说,他的家境还算殷实,前妻未能接续香火,所以,身边也无拖累。听了这番说辞,父亲磕磕烟袋锅,慢悠悠地开口了,嗓音虽冷,脸上到底还是有了暖意。可是,姜玉英的想法却同父亲唱了反调——又不是嫁不出去,好端端一个黄花闺女去给人家填房,多没面子!父亲眼睛一瞪:“你要是嫁个穷光蛋,以后日子怎么过?大人孩子喝西北风去?”说罢,恶狠狠地朝地上啐了口唾沫。女儿像突遭风寒,肩膀瑟瑟地缩紧了。
半年后,她出阁了。
迎亲的小毛驴就像新娘一样形单影只,不同的是,它早已习惯了扮演这样的角色。待到掀起盖头,姜玉英的心里“咯噔”一下,新郎居然比自己矮了半个脑袋!再匆忙瞥上一眼,那直撅撅的头发和脸上直撅撅的线条透露了基本的性格信息:这是一个脾气倔强的男人。
过门第二天,新娘子去挑水。看着她拐着小脚,扭动腰肢,在街头扎堆的女人自然少不了交头接耳。“瞧瞧,那身量,比她男人还猛实。”“啧啧……瞧那身板,十有八九生个虎崽子。”一年后,村民的议论果然应验。两年后,她又生了一个丫头。对于她的表现,婆婆和丈夫自然感到满意。老话说得好:儿女双全福满堂。一个子加上一个女,不就合成了一个“好”字嘛!日子久了,姜玉英在村里也有了不错的口碑。因为,她从来不嚼婆婆舌头,待人总是和和气气。所以,一些人认为,她是东凤凰崖村最本分老实的媳妇。正由于此,妇救会主任才抱着乳儿找上门来。
没等丈夫回话,婆婆先开口了:“八路军是为咱老百姓打天下,人家连死都不怕,咱帮人家抚养个孩子是应该的。”阖家响器,一锤定音。姜玉英迫不及待地接过襁褓,婴儿半睁半闭的眼睛忽然张开了,那痴迷的眼神让人觉得,她似乎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姜玉英的心尖忽悠一颤,这是前世今生的一个约定吗?蓦地,婴儿发出一声古怪的呻吟,噢,饿了,肯定是饿了。姜玉英立马解开衣襟,乳房刚凑上去,小家伙就一口叼住奶头,贪婪地吮起来,频率密集,声音颇大,“咕咚——咕咚——”就像跌落山崖的溪流坠入深涧似的。“不急,不急,慢慢地,别呛着。”姜玉英轻声细语。矫凤珍笑着调侃道:“吃奶能吃出这么大的动静,我还从来没听见过。这个小丫头,真是饿死鬼托生的。”
家里多了一个新成员,原本闹哄哄的小屋声音更嘈杂了。姜玉英发现,八路军的娃娃哭起来也跟自己的孩子不一样,别看嘴巴只有樱桃大小,能量实在很惊人呢!你瞧,只要两片小巧的嘴唇抿成喇叭形,小屋里即刻涛声激荡,若非亲眼所见,恐怕很难想象,人之初竟有如此气壮山河的魄力。
每次喂奶,她都要先紧着仙儿吃饱。待到她的小肚皮舒舒服服膨胀起来,小家伙就会一声接一声地咿呀着,尖尖的、带着奶味儿的声音在小屋里微微颤动着。总算轮到女儿了,她刚吸了两口,就吐出奶头,“哇”地哭了。悸动的音波透着愤怒,也透着困惑:奶水呢?为啥没有奶水了?哭了两声,又裹住奶头,吮了几口,又哭了。姜玉英只好向婆婆求援:“妈,奶不够了,打点糊糊给二嫚吃吧。”然而,女儿的反应表明,她对这样的补救措施同样是很失望的。听着不满的啜泣声,姜玉英在心里喃喃自责。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无能的母亲,真的,最无能的。
除此之外,还有让人闹心的事。
按理说,娃娃小的时候,觉多。仙儿倒好,吭吭叽叽老半天,好不容易哄着了,浅浅地眯上几分钟,眼皮又睁开了。姜玉英苦着脸埋怨道:“这是鸡打盹吗?不好好睡觉,怎么长个?”尤其当夜幕拉开,小家伙变本加厉哭起来,全然一副混不吝的架势。刚一出声,苍白的小脸蛋陡然涂上一层绯红,嘴唇琴弦般震颤,频率之快,简直不可思议。姜玉英赶忙把她抱起来,借着油灯的光,只见仙儿眉毛愤怒地扭曲着,犹如两条蠕动的蚯蚓。拍呀,哄呀,小家伙不依不饶,哭得愈发放肆。一会儿的工夫,脸蛋由绯红变为青紫,给人一种将要室息的恐惧感。没办法,姜玉英只好挪下炕来,颠着小脚,抱着晃着,走来走去。哭声一点点低下去,也说不清到底溜达了多久,终于,姜玉英轻轻地嘘了口气,小心翼翼放到炕上,不料,“嗷”的一声,刚刚结束的演出又重新开始了……
一天,好不容易哄仙儿睡着,突然听见有人吆喝:“鬼子来了,鬼子来了——”顿时,街巷里人声嘈乱,脚步杂沓。姜玉英“蹭”地从炕上弹起来,一边招呼正在院里玩耍的儿子,一边催促婆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她飞快地解开衣襟,把仙儿放进去,拢上衣襟,外面,再裹上一床小被,胡乱找根草绳往腰里一扎。很快,面临后街的窗户被推开了,大人、孩子像扔麻袋一样甩出来,没等脚跟站稳,就匆忙加入了逃难的行列。姜玉英上边裹着仙儿,下边牵着儿子,拼命扯动一双小脚,跑啊,跑啊,没多久,抱着孙女的婆婆就落到后面了。姜玉英停下脚步,一只手叉着腰眼,如同缺氧的鱼儿一样张大嘴巴,胸廓费劲地起伏着。等婆婆上气不接下气地撵上来,姜玉英说:“咱跟不上,就别跟了。人多目标大,容易让鬼子看见。他们往南边跑,咱们干脆往北山躲吧。”喘息片刻,她们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跑去了。山路弯多坡陡,坑坑洼洼,婆媳俩摇摇晃晃,深一脚浅一脚。突然,姜玉英一脚踩空,仰面朝天从斜坡上摔下去。惊魂甫定,她慌忙看看孩子,只见仙儿惶惑地瞪着大眼睛,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姜玉英挣扎着,想撑起来,刚一用劲,大腿根迸出锥心的刺痛,坏了,右腿不敢动弹了。婆婆连拉带拽,折腾了好一会儿,姜玉英方才咬着牙,一瘸一拐地朝山坳里走去。数月后,疼痛逐渐消失了,然而,跛脚的姿态却永远固定下来。咳,这一跤摔的,好惨呐!
不经意间,夜幕垂落,光线渐渐暗下去,仿佛谁在天上涂了一层墨。或许是涂得太多了,墨汁一滴滴坠下来。哦,下雪了,密密匝匝的白线织成一张扭动的大网,开始覆盖茫茫山野。风也趁火打劫,“呜呜”地吼起来。凛冽的寒气挟着雪花频密地灌进姜玉英的衣领,她激灵一下,赶忙把衣服裹得更紧些。好歹折腾到一个叫龙须沟的山坳里,没等坐下喘口气,女儿“哇”地哭起来。哭声是有传染性的,顷刻间,尖细的声音就从姜玉英怀里窜出来。“饿了,饿了。”婆婆连声嘟囔,姜玉英麻利地解开衣襟,怀里的哭声戛然而止,可女儿的哭声却更泛滥了。姜玉英对婆婆说:“妈,你先抱着二嫚到那边躲躲,别让她看见我喂奶,不然的话,她哭得更厉害。等我喂饱了仙儿,再喂她。”婆婆沉默了片刻,抱着孙女躲开了。很快,哀啼渐息,可没多会儿,又哭声大作。不过,颤音持续了短短十几秒钟,就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原来,情急之下,奶奶把自己干瘪的乳头塞进孙女嘴里,小家伙一口叼住奶头,饥不择食啊!只见小脸蛋在奶奶毫无生气的胸脯上使劲蠕动着,她恶狠狠地吮着奶头,几颗乳牙也不停地啃啮。然而,乳房俨若熄灭的死火山,里面的岩浆早已枯竭。她吮了几口,吐出左边的奶头,又衔住右边的奶头,拼命地吮啊吮,小脸儿涨得青紫,最后,彻底失望了。哭声复起,有些嘶哑。奶奶于心不忍,只好抱着孙女颠颠地跑过来,央求儿媳妇说:“多少给二嫚喂两口吧。”姜玉英接过女儿,轻轻吸了口气,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当妈的能不心疼吗。可是,这边刚吃了几口,仙儿又不管不顾地哭起来。姜玉英犹豫了一下,毅然拔出奶头,把孩子递给婆婆。婆婆没吱声,但脸上的表情却把心思暴露了。姜玉英解释说:“宁肯让自己的孩子遭点罪,也不能让八路军的孩子受委屈。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然的话,万一有个好歹,俺咋给人家交代呀!”婆婆想说句什么,却又嗫嚅着,无话可说。少顷,背过身去,看不见她的神情,只看见她的肩头微微颤抖。女儿大概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绝望的哀号透着不甘的挣扎。姜玉英明显感觉到哭声的压迫,倚着树干的身子一寸寸地滑下去。恍惚中,她看见哭声结成冰花,冰花又凝成冰面,她听见,冰面下潜流涌动,那是感情的悲咽啊!
下半夜,女儿终于没了动静。因为连冻带饿,可怜的小家伙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天亮的时候,女儿的小脸、小手涂了一层暗灰,人像霜打的茄子,蔫蔫的。没进家门,就开始咳嗽,额头滚烫,仿佛灼着炭火。呼吸也变得急促,张着小嘴,胸廓费劲地起伏着,好像喉咙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似的。姜玉英慌里慌张地把奶头杵过去,糟了,孩子竟然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姜玉英的头皮“嗡”地一炸,“吃奶,嫚儿,吃奶呀!”女儿不为所动,失神的眼珠像沾了一层灰,乌蒙蒙的。母亲急了,伸手去拍女儿的脸蛋儿,小家伙搐动了一下,随即,爆出一串激烈的呛咳。捱了一天,病情明显恶化,在没有进食的情况下,孩子居然恶心呕吐,并伴发腹胀、腹泻。很快,又出现烦躁不安和谵妄的症状,继而发生肢体抽搐乃至惊厥。待到第三天夜里,小家伙已经气息奄奄。姜玉英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倚着土墙,眼巴巴地守护着。天傍亮的时候,实在困极了,迷迷糊糊睡过去,不一会儿的工夫,突然惊醒,抬手一摸,孩子小脸冰凉,一丝鼻息也没有了。她身子一抖,耳边“噗啦”一声,尖锐的恐惧感像被惊飞的夜鸟掠过头顶。紧接着,滚烫的泪珠夺眶而出,“砰”的一声砸在女儿冰凉的脸蛋上。她呜呜地哭了,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当黎明窸窸窣窣走进小屋时,她仍然紧紧地搂着孩子,让孩子沐浴在母爱最后的晨曦中。母女俩的脸上都笼着一层圣洁的光辉,从旁边望过去,宛若一尊青铜雕塑。此时,这盘普通的农家土炕变成了一座生命的祭坛,生与死的歌咏漾起亦喜亦悲两个声部,伴着深情的旋律,一个从梦乡归来的小女孩又看到了新鲜的霞光,而另一个小女孩却被黑暗永远掳走了。
丧女之痛让丈夫的心情变得十分暴躁,他的额头猛地爆出一条青筋,如同树根裸出地面。“你咋看的孩子!”气咻咻的谴责脱口而出,在小屋里横冲直撞,把姜玉英吓得手足无措。她满眼泪花地望着丈夫,想要开口,喉咙里却打了一个结儿。看到儿媳妇可怜的样子,婆婆发话了:“小嫚害病,当妈的有啥法子?孩子没了,你上火,玉英就不上火吗!”男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腚蹾到土炕上,一连几天,他都阴着脸,没同媳妇搭腔。
或许,情绪的影响能够潜移默化。随后几天,仙儿表现得很乖巧。喂饱了奶,稍微拍几下,就会安安静静睡上一觉。醒了也不像从前那样哭闹,一双乌溜溜的眼珠转来转去,小嘴里不时涌出咿呀声,就像花朵上散发的芬芳。
很快,生活恢复了以往的节奏。看上去,姜玉英的神色平静,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不经意间,忙忙碌碌的一天过去了,夕阳悄然滑落,新月挂上枝头。夜深人静,天地沉寂。突然,老宅里响起一阵“嘤嘤”的啜泣。“醒醒,玉英——”是丈夫的声音。眼皮眨了一下,好不容易睁开了。迷惑的目光透着惊恐,这是一个从睡梦中突然惊醒的人才有的眼神。“咋了?又做梦了?”她怔怔地望着丈夫,突然清醒了。“我看见二嫚回来了,就坐在道边的石头上,朝着咱家大门哇哇地喊,把我喜的呀,赶紧叫了一声,她一看是我,把头一扭,就没了……”丈夫一时无语,闷了一会儿,粗声粗气地说了一句:“寻思那么多,有啥用?睡吧。”
正是因为心中有了隐痛,姜玉英照料仙儿时,更喜欢唠叨了。
小丫头认真地盯着姜玉英,听着听着,好像明白了什么意思,突然咧嘴一乐。姜玉英用手指轻轻碰碰她的小手,嚯,反应挺快,居然紧紧握住,还蛮有劲呢。自个儿躺着的时候,小手、小腿不停地挥呀,蹬呀,尖细的嗓音长一声,短一声,吹哨子似的。那天,小家伙莫名其妙地笑笑,接着,咿咿呀呀。突然,姜玉英听到一声短音,是喊妈吗?虽然混沌,含糊,但做母亲的依然感到了莫大的惊喜。一瞬间,曾经的操劳得到了完全的补偿,一个满足的微笑从她嘴角漾出,就像一朵苦菜花悄然绽开,舒展而又明媚。
冬去春来,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
日子是什么?日子不就是人生的苦辣酸甜,人性的美丑善恶吗?
此时,那个叫仙儿的小丫头已经厌倦了土炕,对尝试走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她扶着炕沿,眼里显出紧张的神情,稍事犹豫,突然一撒手,跌跌撞撞迈开步子。姜玉英颦眉蹙额,一只手往前探着,另一只手抵着肋骨,笨拙地挪着小脚,边追边喊:“慢点,别摔着。哎哟,我的小祖宗!”
一天,丈夫接到通知,和村里一干精壮劳力去前线抬担架。临行前,他小心翼翼地把仙儿揽进臂弯,目光变得十分柔和。眼前的一幕让姜玉英颇感意外,结婚这么多年,她还是头一次发现,言行粗糙的丈夫内心竟如此细腻呢!
一周后,神情疲惫的男人回来了。一进屋,发现炕上睡着一个陌生的小丫头,仙儿却不见了。他疑惑地问:“仙儿呢?”姜玉英回答:“让育儿所接走了,这不,又送来一个。”“多大了?”“不到一岁,刚断了奶。”正说着,孩子醒了,哼哼唧唧地哭起来,姜玉英轻轻拍打着,安慰道:“不哭,妞妞不哭,听话啊……你看,爸爸回来了。”说着,扭过脸来对丈夫说,“村长回来学给我听,育儿所的领导看到仙儿长得白白胖胖,可高兴了,一个劲地表扬咱呢。”
和仙儿相比,妞妞的性格更为活泼。吃饱了,睡足了,她总是自顾自地说呀,动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姜玉英笑眯眯地望着妞妞,喃喃自语,你听听,这小嘴一天到晚都不闲着,到底都说些啥呢?入伏之后,天热起来,妞妞出汗太多。怕孩子喝凉水闹肚子,姜玉英破例点上柴火,每天烧几回开水伺候着。至于家里其他人,依旧像从前那样,抄起水瓢,咕咚有声。乡下人嘛,喝凉水早就习惯了。
为了给妞妞补充营养,姜玉英特地养了两只母鸡,“咯咯哒,咯咯哒——”下蛋了。香喷喷的鸡蛋羹刚端上炕桌,妞妞就眉开眼笑地扑上来,哥哥眼巴巴地在旁边瞅着,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母亲的安抚和劝说带有启发的性质:“你已经长大了,妞妞还小呢!当哥哥的不能和妹妹争吃的,对吧?”儿子眨眨眼,使劲把口水咽回肚子里。无论如何,当哥的总得装装样子吧。
很快,妞妞摇摇晃晃下了地,不过个把月的光景,屋里、院里就待不住了。出门一看,眼界大开。从此,逛街就成了小家伙热爱的事情。有时候,刚喂了两口饭,她就急着往外跑,姜玉英只好拐着小脚撵出去,跟在屁股后面絮絮叨叨,哄着喂她。吃着,玩着,突然要拉屎。于是,她垂下小脑瓜,双手扯着裤子,满不在乎地朝路人撅起小屁股。这时,姜玉英就会聚精会神站在一旁,仿佛是对一种行为艺术进行审美。喏,这就是母亲,也只有母亲才具有这样匪夷所思的鉴赏能力。
在姜玉英无微不至的呵护下,妞妞越长越俊俏了,苹果样的小脸蛋,纤巧秀气的尖下颌,尤其是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眸子黑黑的,像油亮的点漆,像晶莹的玛瑙,像清澈的山泉。这边瞅瞅,那边瞧瞧,长长的睫毛忽闪一眨,真惹人疼呐!当然,妞妞喊妈妈的时候,姜玉英感到最开心。她欢喜地应着,向前探出身子。“来,亲亲妈妈。”小丫头挓挲着小手,摇摇摆摆跑过来,一头扎进她的怀里。接着,热乎乎的小脸蛋使劲拱上来,那种痒痒的、带着奶味的甜蜜把她的整个身心都融化了。
就这样,慈母的笑容屏蔽了烽火硝烟,给妞妞的童年留下温暖的记忆。你瞧,低矮的院墙外,鹅黄的柳枝便是春天的风景;村外的小溪边,孩子的嬉闹则是醉人的乡音;沟沟坎坎的坡地里,一簇簇随风摇曳的苦菜花便是妞妞的童年了。童心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童趣像鸟儿一样在贫穷的天幕下展翅⻜翔,而深深的母爱显然是贫困中唯一奢侈的东西。
妞妞三岁时,被育儿所接走了。
母女分别的那一刻,姜玉英心如刀割。望着突然出现的陌生人,妞妞显然意识到什么,还没等保育员俯身抱她,小嘴一咧,放声大哭。顿时,姜玉英泪眼蒙眬,小屋里的光线变成了晦暗的浅蓝色。保育员和蔼地笑笑,毅然抱起孩子。妞妞急了,拼命挣扎,小手连揪带抓,保育员往后仰着脸,一边躲避,一边仄歪着身子走出小屋。姜玉英抹着眼泪,刚想撵上去,又迟疑着停下脚步,倚着炕沿的身子慢慢矮下去,终于,被凄厉的哭声彻底压垮了。
直到烧饭的时候,她依然失魂落魄地萎在土炕上,眼神蒙眬,雾茫茫的。一觉醒来,姜玉英明显憔悴了,失了水分的脸庞如同一爿燥土,原本清澈的眼睛也缺了光泽。难怪会有一夜白头的说法,殊不知,思念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煎熬啊!

姜玉英夫妇
一有空,姜玉英就会坐到门口,抻着脖子朝村头张望,嘴里时不时地絮叨着什么。有村民搭讪说:“妞妞一走,你轻快多了。”没想到,一句话戳到正在渗血的份口上,姜玉英脸色苍白,眉眼倒挂。“咳,快别提了。一时瞅不着孩子,我就抠心挖肝的。真想去看看她,又不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咱跟谁打听啊?”
过了些日子,人们发现,那双执拗的小脚又把沉沉的思念牵到村头的大树下。姜玉英手搭凉棚,眯着眼,痴痴地朝崎岖的山路张望,见人路过,她就絮叨:“真想孩子呀!你说,她俩还能回来吗……”

(扫码听书)
(节选自唐明华《乳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