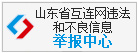第一章 大爱如天
泪光里的微笑
与姜玉英的经历有所不同,姜翠芝之所以成为乳娘,起因和乳儿没有任何瓜葛。
那天,她去挑水,在街上同村支书打了个照面,对方突然想起什么,停下脚步,招呼了一声:“方印家的,跟你商量个事。”她停下脚步,神情有些困惑。

姜翠芝
“啥事呀?”“八路军的兵工厂现在搬到了东凤凰崖,眼下正缺人手,村委寻思,厂子在你娘家,吃住也方便,你能不能回去帮把手啊?”八路军的兵工厂?姜翠芝盯了支书一眼,没等脑子想明白,舌头就沉不住气了。“啥时候去?”“当然越快越好了。”“行,我回家拾掇一下。”支书满意地点点头,眼角的鱼尾纹悄然舒展,脸上的笑容灿烂了许多。
得知媳妇自作主张,丈夫张方印恼了,两只瞳仁忽儿挤成窄窄的墨线,忽儿撑宽,变暗了。终于,喉咙里响了两下,闷闷地甩出一句话:“孩子咋办?”“我带着。”丈夫使劲咽口唾沫,藏在喉结下面的火山骤然喷发:“你说得倒轻巧,兵工厂的活是你出去挑担水、推个磨,一时半会就忙完了的?你一扑拉腚就走,家里这一摊子撂给谁?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和家里商量商量,看把你能的!”心脏“咚”地撞了一下胸口,姜翠芝像遭了钝击似的愣在那儿。结婚两年来,她还是第一次看见丈夫发火。她在心里悄悄数落自己:姜翠芝呀,姜翠芝,你真是猪脑子,这个家到底谁主事你不知道啊!然而,就在这时,一个细小的声音从身体的某个角落冒出来:已经答应村里了,说话不算数,多丢人呐!她想辩解,但不知为什么,喉咙里像窝了一团草,嘴角徒劳地牵动了一下。忽然,窗外传来孩子们的喧闹,肆意的聒噪让她心乱如麻。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丈夫一直绷着脸不吭声。她偷偷瞥了一眼,又赶紧把视线挪开了。闷头吃罢,男人把碗一推,突然拾起昨日的话头:“兵工厂的事比家里的事要紧,人家需要,该去,去吧。”女人喜出望外,发自内心的笑容一股脑地从眸子里涌出来,绽成窗外一树热闹的槐花。
匆匆收拾一番,她就抱起三个月大的女儿,骑着毛驴上路了。时值暮春,曾经寂寞的山野早已变得热闹、活泼。春天是恋爱的季节。野花受了春光的诱惑,远远近近连缀一片,铺排成蜂蝶的婚床;野草受到春风的邀约,深深浅浅摇曳多姿,颇有伴娘助兴的效果。两年前,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顶颤巍巍的花轿就是沿着这条熟悉的山路把她抬到婆家。那扇窄窄的轿门无异于命运旅途上极重要的关口,咫尺之间,心神忐忑的新娘子便跨过了人生的楚河汉界。
姜翠芝的娘家在崖子镇东凤凰崖村,父亲是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1924年,刚过立冬,年轻的母亲开始临盆,一番挣扎过后,嫩生生的小丫头便在血色狼藉的土炕上刻上了自己的生辰八字。两年后,她有了一个弟弟,再后来,又添了一个妹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个模样俊秀的小姑娘性格开朗,快人快语,那张秀气的小嘴颇有语言天赋,正说着话,清脆的笑声蓦地漫开。待到第一个本命年,她似乎一下子挣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及至年底,个头便蹿到一米七。模样楚楚动人,搭眼一看,光鲜的脸蛋儿如同一只漂亮的首饰盒,清澈的眼神仿佛山溪出涧,流动的波光淹没了脸庞的其他部分。所以,当后来那个注定要成为她丈夫的男人见到她时,一定会心旌摇荡,迷失在她含情脉脉的目光里。事实再次证明,面容姣好的姑娘必定不乏媒人提亲。比较而言,父母对西井口村的张姓后生尤其中意。张家世代经商,见多识广,外面人缘活络,家里宅富地肥。择婿大户人家,父母当然求之不得,可女儿却面从腹诽。是啊,身为女人,她知道婚姻是改变命运的大好机会,但素不相识,光凭媒人撺掇就忙着谈婚论嫁,她总觉得心里发虚,不踏实。到底憋不住了,冲着媒人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他长得到底咋样?不会是歪瓜裂枣吧?”话音未落,父亲当场爆了粗口,她像遭了击打的鸟贝,“吧嗒”一下,闭嘴了。
当然,缄默无法化解疑虑。
好在时隔不久,悬念便被迎亲的花轿彻底终结。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喜剧桥段:撩开轿帘的一瞬间,堵在胸口的那坨东西“轰”地粉碎了。新郎个头挺拔,神情俊朗,一双坦诚的大眼睛嵌在国字脸上,目光温暖,笑意吟吟。毫无疑问,用传统的审美标准去衡量,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体面男人。伴着锅碗瓢盆的交响,她的感受由浅入深:丈夫性格沉稳,平日里少言寡语,碰上不熟悉的人,话更金贵。起初,她被表象迷惑,以为他像印象中的许多男人一样情感粗糙,后来,才逐渐觉察到,丈夫其实心思缜密,其根据在于,他对生活画卷的每一处描绘都用了精细的工笔。譬如,油灯的光影小,容易伤眼,女人每次做针线活的时候,他都把浸在油里的灯捻挑得大一点;再譬如,冬天浆洗双手容易皴裂,赶集的时候,他特意买回一盒蛤蜊油……这是一种默默的呵护与关爱,如同一件贴身的衣服,用知冷知热的包裹传达出一般男人少有的细腻与温馨。女人总是容易被感动,有时候,男人一个关切的眼神就足以让她反复回味。庆幸之余,她暗自嗟叹,所谓的美满婚姻,只能是机缘巧合才得以实现,进而言之,这种幸福只能来自上苍的恩赐。时隔两载,她又不知不觉地走向一个利害攸关的时间节点,从故事后续的情节看,正是重返娘家的这次颠簸,不仅把一个幸福家庭,也把相关者的命运走向彻底改变了。
回到娘家稍事安顿,她就出现在兵工厂的被服车间里了。
“太好了,你来得真是时候。你看看,就这么几个人,哪能忙得过来?把我给愁的呀!”车间主任指着乱七八糟的棉衣介绍说,“表和里机器都缝好了,咱们就干后边的活。”说着,困倦地眨眨眼:“催得紧,没法子,大家都辛苦点吧。”姜翠芝会心一笑,似乎是说,不就是干活吗?没啥大不了的。喏,这就是山里的女人,在苦日子里泡惯了,像极了山上的野草,看上去细细柔柔,骨子里却很有韧性呢!
几分钟后,她已经完全进入角色。
但见那枚缝衣针深入浅出,娴熟而轻盈,交织出舞蹈般的韵律。身旁的姐妹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一个年轻姑娘兴奋地嚷道:“哎哟,你的手可真巧啊!”女孩叫田明兰,山东莱阳人,和姜翠芝同岁,不过生日略迟。小田是个命运多舛的农家女。七岁时,父亲病故,九岁那年,做了童养媳。1939年,八路军第五支队驻泊她的家乡沐浴店镇西朱兰村,年仅十五岁的田明兰毅然投身革命,成为支队辖属被服厂的工人。小田个子不高,模样可人,脸蛋儿圆圆的,眉清目秀,一颦一笑都透着胶东姑娘特有的纯朴之美。有时候,人与人的交往实在是一件很玄妙的事情,也许倾盖如故,抑或白头如新。谁也没有想到,看似偶然的姐妹相识,竟促成了日后一段脍炙人口的爱情传奇。
正埋头干活,姜翠芝忽然觉得乳房发胀,又过了一阵,感觉越发胀了,抬手一摸,触痛明显,硬鼓鼓的。她暗自叫苦:坏了,胀奶了!赶紧躲进犄角旮旯,揉啊,挤呀,好一通忙活。看着白花花的乳汁把土墙洇了一片,她禁不住轻声叹惜:哎,白瞎了!
随后,工作重新开始。絮棉花、上衣领、掏扣眼、钉扣子……在时间的压迫下,熟悉的天光悄悄变质。真的,正午的脸庞刚才还神采奕奕,一转眼,就抽缩成黄昏疲倦的面容。姜翠芝胡乱扒拉了两口饭,又操起家什,接着忙碌。针线的咝咝声在寂静里响得十分清晰,长夜被一点点地缝进棉衣里。
直到过半夜的时候,她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里。没等母亲点亮油灯,就一把揽起襁褓,撩起湿乎乎的衣襟。油灯亮了,光影摇曳,有气无力。借着昏黄的光线,姜翠芝看见女儿脏兮兮的小脸上泪痕蜿蜒,如同适才停止了蠕动的蚯蚓。“嫚儿,嫚儿……”姜翠芝连声呼唤,小家伙迷迷瞪瞪睁开眼,认出母亲,“哇”地哭了。“噢……可把嫚儿饿坏了。”她麻利地把奶头塞进女儿嘴里,“吃吧,使劲吃。”显然是吮吸过猛,小丫头突然呛了一口奶,结果,气管痉挛,咳嗽不止。姜翠芝心疼地咕哝道:“哎哟,看把嫚儿给饿的,都怨妈,都是妈不好!”
没过几天,车间摸排统计谁有奶水。主任的解释直截了当:“咱们隔壁的育儿所奶不够吃,厂长的意思是让咱们的人当个不脱产的奶妈,帮着八路军奶孩子。”姜翠芝二话没说,痛痛快快报了名。歇晌的时候,小田悄悄凑过来。“大姐,咱们有的人不实诚。”姜翠芝不解其意,小田扭脸朝倚在墙根的女人努努嘴:“她明明有奶,刚才主任问,你没听她咋说的?”翠芝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有就是有,干吗要撒谎呢?”“耍心眼呗,怕亏了自己的孩子。”
听到女儿报名的消息,母亲先是一愣,接着,闷声闷气嘟囔开了:“你给八路奶孩子,妈不反对,我怕的是,万一走漏了风声,小鬼子不来祸害咱吗?”女儿的回答振振有词:“八路军为啥打鬼子?还不是为了咱老百姓?现如今,人家有了难处,咱不应该帮把手吗?再说了,有八路军保护,怕啥呀?”“咳,都当妈的人了,干啥事还是不过脑子。你以为八路军是村口的大槐树,扎在那里一辈子都不挪窝?人家有腿,不定哪天,说走就走了。”女儿还想反驳,但是,从嗓子眼里冲上来的话撞上紧闭的牙关,生生碰了回去,躲在沉默的掩体里,嘴巴虽然不出声,但是,她依然用无声的争辩执拗地守护着认定的道理。好半天,两人悄然无语,就那么默默地相互看着,仿佛都有些不自在。绷着脸抻了一会儿,母亲无奈地叹了口气。
翌日上午,统计名单新鲜出炉。
按照事先约定,到了喂奶的时候,姜翠芝就放下手上的活去了育儿室。撩开衣襟的刹那间,这位农家妇女的人生价值骤然凸显:她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事情。旋即,孩子的小嘴裹住奶头。她觉得,八路军的娃娃吃起奶来劲头似乎格外大,而且,吮吸的动静也格外撩人,就像迎亲时的唢呐声,抑扬顿挫,煞是甜美。头一个还没奶完,保育员又抱来一个。姜翠芝恍然,噢,娃娃们还排着队呢。等到第三个孩子快要喂饱的时候,贪婪的小嘴突然吮出塌陷的颤音,此时,疲软的乳房如同喷发后的火山,经过持续奔涌,岩浆几乎流淌殆尽。不难想象,当女儿的小嘴恶狠狠地叼住奶头时,吮出的失望有多么深刻,哀哀的哭诉有多么委屈。姥姥发现不对劲儿,立刻刨根问底,得知真相后,窝着脸嗔怪道:“见过实在的,没见过像你这么实在的!不多多少少留点奶,自己的孩子喝西北风吗?”姜翠芝哑口无言,心想:也不怪母亲埋怨,人家张姐当时就只奶了两个孩儿。咳,我可真是个死心眼呀!
次日上午,那对恢复了活力的奶头又像正点的班车准时朝娃娃们的小嘴驶来了。第一个喂好了,接着喂第二个,没等喂饱,保育员又抱来第三个。当热烘烘的笑容扑面而来时,姜翠芝突然明白了,世界上还有一种烦恼的幸福叫信任。哎,这是怎样的幸福哟!痛苦、焦灼,好似捧着一个烫手的山芋。她提醒自己:进门之前不是早就打好主意了吗?凭你怎么说,今天也只能奶两个。可不知咋的,这阵子大脑距离上肢似乎格外远,还没等信号传递过去,两手已经把孩子接过来了。你就打肿脸充胖子吧!她一边悄悄数落自己,一边把奶头塞进娃娃嘴里。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性的魅力吧!是的,面对取舍,这个善良的女人没有计较利害得失,而是听从了爱心的驱使。听,急迫的吮吸声又响了,“咕咚,咕咚……”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孩子,心中那根隐匿琴弦一经拨动,便立刻泛出袅袅的悲悯之音。“咕咚,咕咚……”甘甜的乳汁分明是幼小的生命之舟渡过苦难之河的一根纤绳,正由于此,一个新的悬念产生了——家中的女儿嗷嗷待哺,长此以往,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一天,军区首长来车间视察。
首长个头不高,肤色黝黑,两道剑眉线条硬朗,让人想起阅兵场上的分列式。事后姐妹们才知道,原来,那个面似包公的首长就是威名赫赫的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据史料记载,抗战初期,胶东军区所属部队的装备不仅数量稀少、质量低劣,而且,武器弾药亦严重匮乏。在既缺少技术人才又缺少设备材料的情况下,兵工战士白手起家,千方百计攻坚克难,努力保障部队作战之需。1943年5月,胶东军区第一兵工厂试制出首批硝化甘油炸药。就产品原料而言,制造这种炸药及无烟火药需要大量硫酸。因为日伪军严密封锁,采购硫酸极其艰难。为了摆脱困境,兵工战士土法上马,把大瓷缸改成硫酸塔,利用当地硫矿石土法冶炼,经过反复调试,最终,成功报捷。鉴于此,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参谋长贾若瑜亲临现场表示祝贺。交谈中,司令员得知生产操作时工人的衣服动辄被严重烧蚀,便立刻追问:“什么面料可以做工装?”答:“呢子衣服。”司令员马上命令后勤部门把缴获日军的呢子大衣和防毒面具迅速调拨给兵工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硫酸和火药生产过程中的防护之忧。
那天,首长兴致颇高,他这边瞅瞅,那边看看,俨然对蝴蝶穿花般的缝衣针产生了浓厚兴趣。踱到小田跟前,他索性立在那儿,严肃的目光在姑娘的手上、脸上来回逡巡,看着看着,眼角漾出一个不易觉察的笑影,于是,不近情理的黝黑显得生动了。
按照一般的理解,首长的微笑无疑表达了某种赞许。实际上,它的含义早已超出了女工们的理解范畴。这会儿,恐怕谁也没有意识到,运筹帷幄的司令员已经开始谋划一场新的爱情战役。
没过多久,上级领导亲自做媒了。
事情来得过于突然,以至于小田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碍于礼数,她不好当面回绝,一转脸,就满面愁容地找到了姜翠芝。
老大姐同样颇感意外:“许司令?”小田认真地点点头。
姜翠芝“扑哧”一乐:“好嘛,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谁能想到,咱这不起眼的兵工厂能出息你这么个人物,真是啥人啥命,你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呐!”
小田怔怔地盯着大姐的脸,仿佛上面写满了样子古怪的生僻字。“哎哟,我的老大姐,你是开玩笑还是成心作践我?”她一脸不快地嘟囔着,“为这事儿,我都快愁死了。”
“愁么?”
“你看他长得那个样,又矮又黑,岁数还比我大那么多,要是换成你,心里能舒坦吗?”
姜翠芝会心一笑,语重心长地说:“你说的不假,他长得不好看,岁数也大,不过,依我看,将来居家过日子,光靠一张脸管啥用?顶吃还是顶喝?再说了,男人岁数大也是好事,结了婚知道疼老婆。”
小田神情犹疑,想说点什么,又似乎无话可说。觉察到小田的情绪变化,姜翠芝当然要趁热打铁:“田啊,听大姐一句劝,你没爹没妈,家里条件也不好,能嫁这么个男人,就不愁没有依靠了。大姐是过来人,和你说的都是心里话,你自个好好寻思寻思吧。”一番话,说得实实在在,入情入理,终于,姑娘的眸子里漫出一抹暖色的薄雾,就像春寒料峭中的桃树,绽开冷暖自知的花蕊。
不久,田明兰亲手给许世友做了一双新鞋,让姑娘惊诧的是,对方竟然回赠了一颗弹头。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男人解释说:“我一无所有,只有这颗小小的弹头送给你作纪念。你莫看它小,不起眼,我爱惜得很哩。这是万源保卫战时,敌人打进我肩膀里,我自己用刀尖划破皮肉把它抠出来的。这么多年,一直带在身边。”姑娘接过子弹,像得到稀世珍宝似的紧紧攥在手心里。一物定情,厮守终生,这样的信物实在非同寻常啊!
1943年春,许世友和田明兰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喜糖一包、清茶一杯,一群出生入死的战友用欢声笑语簇拥着一对新人。作为新媳妇娘家的代表,姜翠芝理所当然地被奉为座上宾。这是她的高光时刻,瞧,堂堂的军区司令员对其恭敬如仪,这种场面多么令人欢起(当地方言,高兴的意思)。
不料,大喜伤心。
回来没几天,女儿生病了。
因为夜间着凉,小家伙开始咳嗽、发热,烦躁不安。持续数日后,苍白的小脸蛋泛出淡淡青紫,目光呆滞地望着虚空,仿佛无辜的蝉儿被神秘的面筋粘住似的。原先永远都喂不饱的小嘴破天荒地丧失了饥饿感,勉强喝上几口稀粥,不一会儿,全吐了。等到姜翠芝午夜归来,小家伙已经陷入昏迷状态。她急急忙忙抱起孩子,蓦地,肩膀古怪地搐动了一下。天哪!女儿脖子僵硬,身体却软得面条一般。“嫚儿,嫚儿!”嘶喊像石子落进深潭,没有任何回响。顿时,那颗疲惫的心脏像受惊的野兔在胸腔里砰砰乱撞,几乎要从腔子里蹦出来了。时过三更,小丫头突然出现痉挛。紧接着,喉咙里蹿出一串尖利的颤音,身子如同风中的柳条剧烈摇摆,猛地,肩膀抽动一下,车轮爆胎似的完全瘫软了。
第二天下午,西井口村外的一棵栗子树下添出一个小土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之所以把夭折的婴儿埋在栗子树下,是因其谐音(立子)蕴含福佑后生之意。姜翠芝仔仔细细地培好土,又折了一截树枝插在堆前,至此,摇曳的绿影为小丫头办好了认祖归宗的最后一道手续。哦,骨肉分离,咫尺天涯。但是,在灵魂深处,母亲和女儿情感的根须仍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直到天色向晚,她才失魂落魄踅回老宅。一进门,看见男人被一团混浊的烟雾笼罩着。她刚要从旁边溜过去,冷不丁,男人一声断喝:“又干吗!”接着,重重地磕了一下烟袋锅,身子从雾中闪出来,头发梢泛着烟气,眸子里堆满谴责。姜翠芝眼圈一红,怆然泪下。男人顿时慌了神,乖乖,眼泪原来还有如此神奇的功能,只要女人的眼睛泪花一闪,他就失了主意,不知所措。
晚饭一口未动,但心口窝依然堵得满满的。当然啦,饭可以不吃,家务活却不能耽搁。收拾好锅碗瓢盆,又洗洗涮涮,忙完了,她闷闷地缩进墙角。她在跟自己怄气,无论如何,她都不能原谅自己。嗨,瞧这事闹的,她把自己给得罪了。
几个月后,育儿所和兵工厂相继转移,姜翠芝形单影只地返回婆家。
隔年秋,一串瓮声瓮气的啼哭声划破晨曦,丈夫高兴地从门外的小凳上蹦起来。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简直就是拯救了两个大人的神灵,因为他,世界上少了一个饱受妊娠之苦的母亲,多了一个欣喜若狂的父亲。姜翠芝从接生婆手中战战兢兢接过儿子,如同接过一件昂贵的瓷器。看上去,小家伙如同一只刚刚甩掉尾巴的小青蛙,圆滚滚的肚皮随着呼吸一起一伏,白嫩嫩的胳膊、小腿保持着准备跳跃的蜷曲姿态,仿佛随时随地都会从她怀里蹦出去。吮吸声乍响,姜翠芝悲喜交集:感谢上苍眷顾,给了自己将功补过的机会。事情明摆着,那个男婴不仅帮助母亲顺利完成自我救赎,而且,也让一脉香火成功延续。
1944年8月15日,胶东军区向胶东军民发布动员令,要求分区独立作战,相互配合,形成全面反攻的战略态势。1945年1月26日,胶东行署决定,牟海县改称乳山县,命名依据则为境内南部的大乳山。同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各地迅速扩充兵源,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迅即,乳山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丈夫张方印毅然报名,光荣入伍。
临行前,他笨手笨脚地抱起儿子,泛着奶香的小家伙呆萌萌地望着他,眼睛眨了眨,忽然“哇”地哭了。男人有些慌乱,连忙摇动胳膊。随后,呢喃着俯下脸,用鼻尖在儿子的小脸蛋上轻轻蹭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女人。“给我看好儿子。”夫妻一场,这是他留给姜翠芝的最后一句话。
丈夫走了,她的心一下变得空落落的。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叫作思念的东西悄悄从心底渗出来,如同浓度很高的硫酸,把情感的神经灼蚀得好痛啊。眼巴巴地盼了一年,终于,有消息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记忆的底片上,丈夫的最后一幅影像竟是空白。
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太阳面色苍白,几朵憔悴的云也散发着忧伤的气息。不知何故,村干部把她请到村委会。一上来,支吾着不敢说实话。一个说:“大妹子,等全国解放了,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另一个说:“是啊,大米白面管够,一顿饭一个大苹果。”姜翠芝越听越糊涂:“你们到底要说啥呀?”村长叹口气,一拍大腿:“咳,跟你说实话吧,方印他……”话音刚落,她一头栽倒了。
接下来,是一个血泪斑斑的不眠之夜。
透过蒙眬的泪光,她看见丈夫那熟悉的身影跌跌撞撞向自己走来。哦,一个个遥远而又模糊的生活场景顿时变得异常清晰,轻轻地,从她眼前依次划过,慢慢浓缩进这个伤心欲绝的凄凉夜晚。及至天色微明,她撑着炕头非常吃力地爬起来,看上去,颤巍巍的身体对支撑的双臂仿佛是个极重的负担。忽然,嘴里觉着不对劲儿,哎哟,门牙怎么掉了!她抬手一摸,发现牙齿就像狂风肆虐后的树苗,根系松动,摇摇晃晃。随后,事态逐渐升级,不过一天,两排牙齿便七零八落掉了大半,仅剩几颗磨牙茕茕孑立。一夜之间,年轻媳妇就变成牙床空洞的老太婆,这是多么荒诞的场景啊!捧着一堆血迹模糊的牙齿,姜翠芝心如枯槁,什么念想也没有了。
不知什么时候,一轮明月挂上树梢。月光筛进窗来,照着灶边散发着霉味儿的麦草,如同照着看不见的忧伤。后来有人回忆说,那天晚上的月亮似乎不同以往,看上去,像是浸透了清凉的泪水,湿漉漉的。她佝偻着腰身,僵僵地倚着墙角。突然,脑海里火花一闪,瞬间的光芒照亮了心中最隐秘的角落。她惊愕地睁大眼睛,呀,一个陌生的黑影静静地立在那儿,五官模糊的脸上浮出诡异的笑容,她倏地一个寒战,死神?没错!她忽然有了一种彻头彻尾的解脱感。多少年了,她对死亡一直心存恐惧,可眼下,感觉却完全不一样了。她着了魔似的想到可能的结局,她甚至有些奇怪,死神其实很亲切嘛!“事到如今,只要把眼一闭,就一了百了,再也不会遭这份罪了!”想到这儿,嘴角现出一道扭曲的皱纹,眼睛里也闪过一个古怪的笑影。就在这时,夜色中传来丈夫幽幽的嗓音——给我看好儿子!她倏地打个冷战,噩梦被惊醒了。
只隔了一个晚上,那张脸就老了好多年,眼睛则大了一圈,相形之下,脸庞似乎缩小了尺寸,让人觉得,她的眼眶大极了,看上去两个眼球像是漂浮在大海上,而且,眼神凄清,犹如冬天的旷野,苍凉、空洞。
捱过凛冽的寒冬,新生的麦子开始抽穗了。
小暑那天,村干部找上门来,意思是育儿所眼下急需乳娘,希望她能去帮忙奶几天孩子。姜翠芝征求公婆意见,婆婆当场表态:“国军(儿子乳名)他妈,把孩子交给我,你放心去吧。”姜翠芝立即收拾了两件换洗的衣服,匆匆赶往育儿所的驻地田家村。随后,她的怀里就添了一个叫“胜利”的孩子。虽说名字叫得响亮,但精神却显得萎靡不振,快七个月了,咿呀声还是又轻又缓,就像老妇的哀叹透着暮气。不过,第一次吃奶,他就给乳娘来了个下马威。脸蛋儿刚贴上胸脯,小嘴就急切地寻找那团幸福的安慰。姜翠芝“哎哟”一声,疼得直咧嘴,他却不管不顾,可劲儿吮吸。不一会儿,神情变得活泼起来,皱巴巴的小脸蛋也明显松弛了。吃饱了,喝足了,他舒舒服服地哼了两声,笑嘻嘻地咧咧嘴,两片小巧的嘴唇如同新鲜的花蕊赫然绽放,牙龈上,刚刚露头的两点白釉一闪一闪的。姜翠芝也笑了,只不过,笑容里透出了隐约的咸味儿。
入伏后,天气越来越热。
知了的聒噪如同滚沸的热水哗哗流淌,涌动的热浪爆出了隐约的碎响。酷暑难耐,小家伙起了痱子。好歹扛过白天,天一擦黑,姜翠芝就点燃麦糠熏蚊子。令人苦恼的是,蚊子倒是熏跑了,孩子也被熏得眼泪汪汪,咳嗽、憋闷。为了让孩子睡个安稳觉,她抱着小胜利坐到院子里。下半夜,露水重了,再抱回屋,晃着蒲扇驱赶蚊子。这一宿,孩子美美地睡到大天亮,大人却实在熬坏了。
三伏天日子难耐,三九天也同样遭罪。上半夜,因为灶膛余热尚在,土炕还有些热乎气,等到下半夜,就完全凉透了。怕孩子着凉,她就把小家伙放到肚皮上,睡着睡着,小鸡鸡忽然变成小水枪,“哗啦啦”,把她尿醒了。“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了你的债?哪有这么祸害人的?”她揩着水淋淋的身子喃喃数落,浸透了母爱的无奈表情让人想起了瑟瑟秋风中摇曳的苦菊。不多会儿,小家伙又趴在肚皮上憨憨睡去。她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恍惚中,从寂静的深处传来小孩子隐隐的哭泣,她屏住呼吸,是的,那是儿子的声音。她呻吟似的哼了一声,真是委屈他了。唉,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当妈的有啥法子呢?
就这样,一盘普通的农家土炕变成一座撼人心魄的时代舞台,日复一日,同样普通的女主角都在重复一幕伟大的演出。于是,人们看到,她用博大的母爱把悲剧演成喜剧,把哽哽悲咽变成朗朗笑声。
春末夏初,育儿所再度转移。此时,小胜利已经断奶,这就意味着,属于姜翠芝的使命已经圆满结束。
乳娘姜翠芝的小儿子张启宝和爱人经常翻看老照片,回忆过去的事情。他告诉作者,1986年他花了将近60块钱,给母亲镶了满口牙,直到母亲临终前,还唠叨说,这口牙真好使。

返回娘家那天,路边的苦菜花开得正艳。走着走着,她忽然来了兴致,采了一朵戴在头上,随之,脸上漾开一个明丽的笑容,忽然想到什么,赶紧把嘴抿住。哦,这个动人的笑靥多像绽放的苦菜花呀,根是苦的,花却是香的。是啊,在那些艰困的岁月里,人们不是一次次地看到了泪光里的微笑吗!清风徐来,如丝如缕,远远近近的苦菜花浅吟低唱,妩媚的金黄显得越发明亮、灿烂了。

(扫码听书)
(节选自唐明华《乳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