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宦海浮沉,从21岁出眉州参加科举走上仕途,到66岁常州仙逝,在长达45年的从政生涯中,以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800多篇文论,构筑起一个波澜壮阔、横无际涯的文学世界,其思想之深邃、著述之丰盈、涉猎之宏阔、成就之卓越,被后人尊为“苏海”。
苏轼一生两次“在朝——外任——贬居”,期间奔走南北15个地方,而在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十五日到任登州太守,只五日又接朝廷九月诏书返京,则是他时间最短的一次地方从政经历。但就因这短暂的时光,却留下一曲曲千古传颂的山水吟唱和一段段关注苍生民瘼的善政情缘。清人张弓有诗赞曰:“赖有公来官五日,三山万古重蓬莱”。
2023年4月,威海市文登区发布城市形象宣传片,与宣传片同主题的宣传语同步在高速路口、户外显著位置闪亮登场。跨越千年,苏轼《与鞠持正书》中的那句话依然文脉充盈、气场强大:“文登虽稍远,百事可乐”。

摄于威海市文登区高速高架桥下
虽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但苏轼对一个地方的赞美,还从来没有如此凝练至简,乐观通透。“苏海”一粟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
(一)尺牍片言,引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随着文登形象宣传片发布,有媒体报道说:“苏轼一生演绎着超旷豁达的传奇,进可安天下,退能山水怡自身,留下诗词佳作无数,在《与鞠持正书》之二中的这句诗,成为文登这座千年古城的形象注解。”①
其实“文登虽稍远,百事可乐”并不是一句诗,而是一篇只有67个字的尺牍中的一个短句。
查《与鞠持正书》之二原文:“知腹疾微作,想即平愈。文登虽稍远,百事可乐。岛中出一药名白石芝者,香味初嚼茶,久之甚美,闻甚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状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为辩,秘之,秘之。”
原文大意如下:“得知您腹部略有小病,想必已经痊愈。文登虽然稍微偏远,但诸事可乐。岛中出产一种称为白石芝的药,香味刚开始如同嚼茶,久之甚美,听说对人体极为有益,我不能不告知于您。白石芝看上去像石耳,却有香味,可以依据此特征进行辨认,保密呀!保密呀!”②
这篇尺牍创作于何时何地,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元丰八年知登州时作。”③另一种说法称:“《与鞠持正书两首》以下俱扬州。”②
从目前证据看,第一种说法仅在李之亮的笺注《与鞠持正书二首》中出现,李坦陈是根据文章内容粗略进行编年,属一家之言,其在笺注中,也引“原本题下注云:以下俱扬州’兹姑从之”进行标注。
据苏轼在登州写的著名题跋《书吴道子画后》所记的时间,他在登州至少待到十一月七日。知登州期间,苏轼还作有歌行体长诗《鳆鱼行》《登州海市》诗等,对登州特产海珍鲍鱼和海市蜃楼进行了热情洋溢的咏赞,离登到朝,他上书《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呼吁朝廷加强海防军事力量,特别是上书《乞罢登莱榷盐状》,呼吁取消登州的海盐专卖,提议“先罢登莱两州椎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朝廷果然采纳了这一建议,登莱两州海盐自主买卖,一直延续到清朝。他一贯关心国忧民瘼的政治品质对和登州的特殊感情深深感动着登州父老。《登州府志》叙曰:“(苏轼)在郡虽未久,然士薰其化,民安其政,恨其去之速。”
综合史料看,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文登虽稍远,百事可乐”创作于在登州期间。其实,苏五日太守之所以留下关于登州的大量诗文,源于补记的好习惯。如他的笔记小品《北海十二石记》,就是在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以端明、侍读二学士知定州,因要求调任越州,留居京师礼部期间,心境抑郁,闲来无事,而做的追记。此时,距他离任登州,已经过去了8个年头。
要想弄清楚“文登虽稍远,百事可乐”写于何时何地,就需要把两篇《与鞠持正书》文章综合考量。
《与鞠持正书》之一原文:“两日薄有秋气,伏想起居佳胜。蜀人蒲永升临孙知微《水图》,四面颇为雄爽。杜子美所谓‘白波吹素壁’者,愿挂公斋中,真可以一洗残暑也。近晚,上谒次。”
大意是:“两日来略有秋天气息,想必您生活安好。蜀人蒲永升临孙知微的《水图》,四面都极为雄壮开阔,正如杜甫所说的‘白波吹素壁’,请您挂进书斋,可以洗尽残暑余热。不久后,我再去问候您。②”
此处提到的杜甫诗句,是苏轼记忆出现的一处“小模糊”,杜甫《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中,实为“白波吹粉壁”。提到“蜀人蒲永升临孙知微《水图》”,在苏轼《书蒲永升画后》中也有记载,《水图》题跋时间为元丰三年(1080年)十二月十八日夜,作于黄州临皋亭西斋。当时,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文中提到“近晚,上谒次”,说明苏轼与鞠持正在同一个地方,相距不太远,但肯定是离开黄州之后的某地。
根据《苏轼全集》称两首《与鞠持正书》均作于扬州的标注和两篇尺牍信息比对,极有可能是在元祐七年(1092年)任扬州知州期间作。此时,已经距他离开登州7年。是年二月,55岁的苏轼任扬州知州,在扬州待了7个月,且时令也符合“薄有秋意”记述。扬州是他为躲避朝廷激烈党争要求外任之地,得到朝廷的准许,因此心里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也从两篇尺牍的语气中得到印证。“文登虽稍远,百事可乐”既说明了他写作时的好心态,也显露出他登州之旅的愉悦心情。上任登州,是他仕途陡然上升的起点,到任登州才五天,朝廷就以礼部郎中召苏轼还朝。元丰八年(1085年)底,苏轼赴京就任。此后,连续升任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直至位居正三品的翰林学士知制诰并兼任帝师。而扬州是他仕途走向高光时刻的另一起势之地。元祐七年(1092年)九月苏轼接到调令,被召回汴京参加郊祀大典,十一月进官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达到他一生中最高的职位。此时,苏辙被任命为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执政之一),两兄弟均身居高位。
(二)莫嫌五日匆匆守,来登州前后竟七次提到“文登”,并留有小楷“文登”二字真迹传世……
苏轼离开登州时写下《留别登州举人》,饱含着自谦意味的“莫嫌五日匆匆守”,是坡翁的真诚表白。
“登州”始置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当时,趁隋末天下大乱而占据文登一带的地方豪强淳于难主动归属唐朝,于是,“武德四年九月,乙卯,文登贼帅淳于难请降,置登州,以(淳于)难为刺史。”(《资治通鉴》)
如今属于威海市的文登区,历史上因秦始皇东巡“召文人登山”而赫赫有名,至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建县,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建县史,是胶东半岛少数千年古县之一。唐宋时期的“登州”,在文献中就有“文登郡”的称谓,如,唐代的《通典》中就有“今文登郡文登县”的字眼,《十道志》(《太平御览》引述)中也说:“登州,文登郡。汉牟平县,属东莱郡。”北宋时期修撰的《太平寰宇记》亦曰:“登州,文登郡,今理蓬莱县。”
宋朝改革唐朝地方行政制度,确立了中央政府领导下的路、州(府、军、监)、县三级政区制。山东大部分地区划归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仅有少数州、县属于河北东路,合计26州(府、军),89县。苏辙在《次韵子瞻病中赠提刑段绎》诗中就有“京东分东西,中划齐鲁半。兄来本相从,路绝一长叹。”的描述。登州、莱州、青州、淄州、密州、沂州、潍州等7州属于京东东路,登州辖蓬莱、黄县、牟平、文登等4县,苏轼就任登州太守时,治所在蓬莱。

参考《山东省历史地图集》绘制的北宋登州行政区域图
苏轼多篇诗文中提到的文登,实为登州之代称。文登作为县名,始于北齐,唐初于文登县地建置登州,登州之名由文登而来,史籍有称文登郡,最初治所在文登县,历经废置重建,治所迁移,唐神龙年间移迁蓬莱,此后文登作为登州的属县,但其名称却较登州为古。由于具有这种地理沿革关系,苏轼诗文中有时求其古雅,或灵活变换称呼,故将登州称作文登。
蓬莱长岛文化资深研究专家吴忠波先生认为,苏轼之所以用文登指代登州,显示出其作为文章大家渊博的文史知识。文登系登州之前治所所在地。东坡先生以文登称呼蓬莱,如同今人以齐鲁相称山东,华夏相称中国。⑤
元丰八年(1085年)八月中下旬,苏轼上任途中路过扬州期间所作《余将赴文登,过广陵,而择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诗为别》首次提及文登。择老,此前为竹西寺住持,此时移住石塔寺。苏轼专程拜访并留诗:“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还逢惠照师。我亦化身东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苏轼被贬五年后被重新启用,到蓬莱赴任,“我亦化身东海去”和“姓名莫遣世人知。”都表现出其意趣脱俗的浪漫和对蓬莱仙境的向往。
苏轼第二次撰文提到文登,是在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初至十五日,在密州赴登州的海行船上所作的题跋《书柳子厚诗》中:“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旁诸峰,真若剑鋩,颂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子厚云:‘海上尖峰若剑鋩,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锋峰头望故乡。’”
苏轼第三次撰文提到文登,是在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二日。《东坡志林》记载,苏轼与同僚在登州日宾楼饮酒作画,并《书自作木石》云:“东坡居士移守文登,五日而去官。眷恋山水之胜,与同僚饮酒日宾楼上。酒酣,作此木石一纸,投笔而叹,自谓此来之绝。河内史全叔取而藏之。”
在《齐州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中,他第四次提到文登:“八年,移守文登,召为尚书礼部郎,过济南长清真相院……”
在长清真相院,苏轼得知该寺院住持僧法泰所建13层砖塔(名全阳塔,今已不存)未有葬物,于是便欲将其弟苏辙所藏的释迦舍利捐献出来,为已过世的父母祈求“冥福”。两年后的元祐二年(1087),法泰赴京师(今河南开封)找到苏轼,拜请舍利,并请苏轼撰写塔铭。出于对佛法的虔诚和对父母的敬重,苏轼郑重其事地用小楷写下《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引》,然后又赠法泰“金一两,银六两,使归求之众人,以具棺椁”。

《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引》拓片
1965年,在拆除舍利塔塔基地宫时,意外挖掘出这件精美书法碑刻,苏轼小楷真实面目遂大白天下。苏轼小楷字字精神,神气完足,堪称逸品。苏轼文辞优美,禅机毕见。法泰主持刻工精细,字字清晰,幸久埋地下,全碑无一字残损,完整如新,完美保存了苏轼小楷的真实面貌,堪称小字传世代表作。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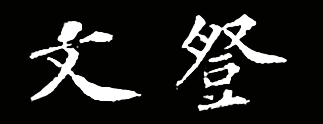
拓片局部放大拼图
苏轼第五次、第六次提到文登,是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至元祐六年(1091年),其还朝后又出任杭州知州时期。在以吏部尚书召回朝廷期间,他对在知登州期间于蓬莱丹崖山旁取弹子涡石数百枚,用以养菖蒲的诗文追记。诗名叙其所由:《文登蓬莱阁下,石壁千丈,为海浪所战,时有碎裂,淘洒岁久,皆圆熟可爱,土人谓此弹子涡也。取数百枚,以养石菖蒲,且作诗遗垂慈堂老人》。
诗中说:“蓬莱海上峰,玉立色不改。孤根捍滔天,云骨有破碎。阳侯杀廉角,阴火发光彩。累累弹丸间,琐细或珠琲。阎浮一沤耳,真妄果安在。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块。置之盆盎中,日与山海对。明年菖蒲根,联络不可解。傥有蟠桃生,旦暮犹可待。”
诗的前半写珠徘般的球石的形成过程,以“孤根”“云骨”形容山崖之陡峭,以水神阳侯砍杀巨石棱角形容海浪的威力,以波涛的阴冷闪光“阴火”形容球石在水中的光采,写得奇警动人。诗的后半用想象笔法抒写对球石爱悦,和由它的产地来源而引起的对登州山海的眷恋。
苏轼爱石,也爱石菖蒲。“石,得之于蓬莱,归而洒于石盆中,注入些许清水,以养菖蒲。面对此一清供,他与老友论‘小中现大’的腾挪。他几乎不是在制作一个盆景,而是在复演大海的浩瀚;他袖回的不是几片弹子窝,而是带回整个东海的信息。”⑥
苏轼在登州期间还淘了一些像芡实大小的白珊瑚圆颗粒准备做枕头。他的《始于文登海上,得白石数升,如芡实,可作枕。闻梅丈嗜石。故以遗其子子明学士,子明有诗,次韵》,诗曰:“海隅荒怪有谁珍,零落珊瑚泣季伦。法供坐令微物重,色难归致孝心纯。只疑薏苡来交趾,未信蠙珠出泗滨。愿子聚为江夏枕,不劳挥扇自宁亲。”
诗中将球石喻为零落的珊瑚、珍珠,诗末“愿子聚为江夏枕,不劳挥扇自宁亲。”用江夏孝童黄香的故事,赞美球石枕的散热宁人之效。
苏轼第七次提到文登,是在元祐八年(1093年)十月二十三日到达知定州任后。这之前的一年时间,他不断遭受弹劾,妻子王闰之八月病故,九月高太皇太后病逝,哲宗即位极不待见苏轼。在写给弟弟的《东府雨中别子由》诗中曰:“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尽显苏轼内心萧索和悲凉。
中山为定州的古称。在定州,他作石芝诗(并引),感慨有登州客送其石芝,念及中山教授马君为文登人,忍着眼痛又题跋《书石芝诗后》。曰:“中山教授马君,文登人也。盖尝得石芝食之,故作此诗,同赋一篇。目昏不能多书,令小儿执笔,独题此数字。”
(三)自笑平生为口忙,美食家苏轼和弟弟苏辙围绕海上仙药石芝发生一系列梦境与现实的唱和,苏轼曾在5篇诗文中提到石芝……
《与鞠持正书》之所以称文登百事可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有海上仙药白石芝。苏轼绘声绘色地拿茶和石耳对比出白石芝的型、色、香味,并故作神秘地让鞠持正不告诉别人,卖萌耍宝,趣态悠然。
白石芝:白色的石芝。《抱朴子·仙药》:“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议有百许种也。石芝者,石象芝,生于海隅名山,及岛屿之涯有积石者,其状如肉象有头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于大石,喜在高岫险峻之地,或却着仰缀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泽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彻如坚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见其光矣。石耳:附着在石面的地衣类植物,可食。”《吕氏春秋·本味》:“菜知美者,昆仑之苹,寿木之华,汉上石耳。”高诱注:“石耳,菜名也。”宋王质《临泉结契·石耳》:“石耳色面黑背紫,柔薄,生深崖危壁,与木耳、地耳皆珍。”
这是他撰文第二次提到石芝。
苏轼在登州期间没有吃过白石芝的记载,但早在贬居黄州期间就开启了他的“吃货模式”,并首次梦到吃石芝。
在《初到黄州》诗中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元丰三年(1080年)五月十一日夜,他竟然做了一个跑到别人院子里折食石芝的梦,并于次日作《石芝(并引)》诗如下。
“元丰三年五月十一日癸酉,夜梦游何人家,开堂西门有小园古井,井上皆苍石,石上生紫藤如龙蛇,枝叶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余率尔折食一枝,众皆惊笑,其味如鸡苏而甘,明日作此诗: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来初匀。了然非梦亦非觉,有人夜呼祁孔宾。披衣相従到何许,朱栏碧井开琼户。忽惊石上堆龙蛇,玉芝紫笋生无数。锵然敲折青珊瑚,味如蜜藕和鸡苏。主人相顾一抚掌,满堂坐客皆卢胡。亦知洞府嘲轻脱,终胜嵇康羡王烈。神山一合五百年,风吹石髓坚如铁。”
苏轼在诗中想象石芝的味道像中药龙脑薄荷但更甜。苏轼在赴定州前居于京都开封期间,有客人携石芝一篮自登州而来相赠,自言海上诸岛,凡岩石向日者多生耳,海人谓之石芝。据说有海上幽人常取而服之,言有大益。苏轼喜得石芝,与弟苏辙共享之,其味如荼,久而益甘。
在这段时间,他在《北海十二石记》第三次次提到登州石芝:“登州下临大海,目力所及,沙门、鼍矶、牵牛、大竹、小竹凡五岛。惟沙门最近,兀然焦枯。其余皆紫翠绝,出没涛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玮,多不识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斓,或作金色。”
苏轼刚到定州,就收到了弟弟苏辙的来信,信中还有一首以《石芝》为题的诗。细读弟辙的来诗,往事历历在目,诗中的一字一句都牵动了苏轼的思绪。苏辙在诗引与诗里写道:“子瞻昔在黄州,梦游人家井间,石上生紫藤,枝叶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折而食之,味如鸡苏而甘,起赋八韵记之。元佑八年。予与子瞻皆在京师,客有至自登州者,言海上诸岛,石向日者多生耳,海人谓之石芝,食之味如荼,久而益甘。海上幽人或取服之,言甚益人。客以一篮遗子瞻,遂次前韵:鸡鸣东海朝日新,光蒙洲岛雾雨匀。一唏石上遍生耳,幽子自食无来宾。寄书乞取久未许,箬笼蕉囊海神户。一掬谁令堕我前,无为知我超其数。此身不愿清庙瑚,但愿归去随樵苏。龟龙百岁岂知道,养气千息存其胡。尘中学仙定难脱,梦里食芝空酷烈。中山军府安得闲,更试朝霞磨镜铁。”
苏轼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于是和诗一首,仍以《石芝并引》为题,第四次写到石芝:“予尝梦食石芝,作诗记之。今乃真得石芝于海上,子由和前诗见寄。予顷在京师,有凿井得如小儿手以献者。臂指皆具,肤理若生。予闻之隐者,此肉芝也。与子由烹而食之。追记其事,复次前韵:土中一掌婴儿新,爪指良是肌骨匀。见之怖走谁敢食,天赐我尔不及宾。旌阳、元游同一许,长史、玉斧皆门户。我家韦布三百年,只有阴功不知数。跪陈八簋加六瑚,化人视之真块苏。肉芝烹熟石芝老,笑唾熊掌嚬雕胡。老蚕作茧何时脱,梦想至人空激烈。古来大药不可求,真契当如磁石铁。”随后,他又在《书石芝诗后》题跋中第五次提到石芝。
(四)苏轼赴任登州,由密州板桥镇码头上船,航行一周左右,经文登海域,绕行成山头抵达蓬莱治所……
对苏轼在登州往返的行迹,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做过极其简短的概述:“苏东坡在六月,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进京。全家开始行动起来,将近元丰八年十二月半,到达京都。”⑧
苏轼是经金陵、扬州、泗州、常州、海州(今连云港)抵达密州的。这一段史料非常清晰。苏轼上次来密州还是在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三日,由杭州通判异地升迁为密州知州,至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两年有余,功业屡屡。9年后再次踏上这片热土,密州父老、儿童遮道相迎,太守藿翔置酒超然台,为寻旧迹并赋诗。⑨
林语堂说的“(苏轼)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自唐始胶州属于密州板桥镇,板桥港这个区域在北宋称为唐家湾,又称唐湾,东临胶州湾海域,水面开阔。公元836年(唐开成元年)日本著名僧人园仁法师回国时,曾在板桥镇海域(密州大珠山)乘船至荣成赤山法华寺。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还记录了一批船人自称“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本是新罗人,人数十有余”。圆仁描述了晚唐时期楚州—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密州—登州一线繁忙的海上交通线,自晚唐以来就是一条传统的航海线,密州板桥镇是这海上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港口。到了宋代,板桥镇港在全国海港中的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因北宋和辽对峙,朝廷明令禁止海船入登州、莱州港,板桥镇自此成为我国五大通商口岸之一,也是北方唯一的海关重镇。
秦汉之际已形成传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沿海诸港起航后,循海岸线向东航行,绕过成山头北上,经渤海至辽东半岛南端,再沿海岸线东行抵鸭绿江口,然后南下至朝鲜半岛西海岸相关港口;若到日本列岛则要经过朝鲜海峡西水道至对马岛、北九州海岸,然后航行到日本相关港口。这一传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继续被民间商船沿用之外,又新开出一条由胶东半岛横渡黄海抵达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新航道。⑩
苏轼乘船抵蓬莱的历史证据,也藏在苏轼第二次提及文登的《书柳子厚诗》的题跋里。⑪
在这篇题跋中,苏轼一如既往地用东武和文登古称代指密州和登州。大意是:我从东武前往文登,在海上乘船行了数日,所见到的道傍山峰,真像剑鋩一样。读柳宗元的诗,知道海上的山峰多是这样。他有诗说:“海上尖峰若剑鋩,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锋峰头望故乡。”
吴忠波、夏婧尧在《苏东坡经古之罘到达登州》一文考证:“十月下旬,苏东坡陆路到达密州。从离开密州时间推算,他应该是十月上中旬自板桥镇乘船赴登州。海行数日,也就是高密板桥、崂山、过威海成山头,到烟台芝罘,古称之罘,东坡所乘的官船径直飘过,再从蓬莱水城上岸。”
从密州到登州,之所以不选择陆路,而走海路,也足显当时陆路交通的不便,更说明板桥镇港的便捷。在整个过海的过程中,苏东坡留下的资料不多。学界和苏作中对此的表述,也是一笔带过。其海路行程时间,据苏东坡《书柳子厚诗》云:"仆自东武(高密)适文登,并海行数日。”这里的数日,应该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吧。
“如同一路行来一路歌,大诗人过海行舟,也与众不同,即使是秋风海浪的情形下,苏东坡也是闲不下来。尽管在船上,进行创作,还是有一些限制。但是,书名人书还是小菜一碟。不知是这时,他正看着柳子厚的诗书,还是适宜于用柳诗表达,他将海路一程,或包括登岸后一段时间,让柳诗唱了主角。他本人只是作了个点评人而已,顶多是随和着发点感慨。出海后的沿途,他能看到的是崂山、田横岛、海阳凤城、乳山口及槎山、石岛湾、成山头、昆嵛山远景、古芝罘沿岸、蓬莱阁及水城。而他能表达的仅是:‘道傍诸峰,真若剑铠’。其他,也许是舟船劳顿等因素,他没有大发感慨,而是让柳诗等登场,他则是书题、评议而已。”⑫
因为苏东坡是乘船由胶东半岛南部环海到达北部登州驻地,而宋时胶东半岛东部俱属文登县境,因此可以确认苏轼确曾航行到过文登海域。
学者李常生著有皇皇五卷本《苏轼行迹考》。在第四卷中,他也注意到苏轼《书柳子厚书》中的海行说,并发出疑问:“或古代陆行不易,部分入海州行至登州?有无过莱州,亦不得而知?”然而他还是凭自己的想象画出苏轼自怀仁(海州)至登州的陆路行迹图:密州—莱州—登州。
其实,苏轼在诗文中也留有到过莱州的证据,只不过,那是他离任登州太守后的返京路线。
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中旬,他从登州走陆路,经莱州、青州、过龙山镇夜宿并留下《跋王氏华严经解》入齐州(济南),年底自郓州(菏泽)出山东入河南商丘,至汴京开封。
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过莱州雪后望三山》就是作于离登赴京过莱州时,诗曰:“东海如碧环,西北卷登莱。云光与天色,直到三山回。我行适冬仲,薄雪收浮埃……”东坡取道青州时,他曾经的“政坛死敌”,原御史中丞、现青州知州李定热情款待了他,他们在诗酒共流连中实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苏轼在给好友滕元发的信中说:“青州资深(李定字),相见极欢,今日赴其盛会也。”继江宁府与王安石和解后,苏轼在青州又与一位严重伤害过他的政敌实现和解。
(五)鞠持正何人?一段待考的历史迷案等待着有缘人破解……
据李之亮笺注,鞠持正:东坡诗集、文集、词集仅此一说,不详为谁。检《万姓统谱》亦无此人。待考。③
网上有说法认为鞠持正为蔡确,因此字持正,不过缺乏实证。但对苏学的研究一直是一代代学人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取得成果的学术开放系统。
苏轼一生交友广泛,自言:“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据无冕学者孔凡礼所编纂《苏轼年谱》,参考六百多种书籍,仅《苏轼交游录》就收录一千三百多人。
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十收有苏轼给友人公弼郎中的一封短简。这个公弼是谁,孔凡礼遍查苏轼全部著作、同时代人著作及地方志等,没有搞清楚。苏轼此简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当时在密州(今山东诸城)。1994年10月11日,孔凡礼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靖华、诸城市博物馆任日新、诸城市史志办主任邹金祥结伴到九仙山中寻访苏轼遗迹。攀山途中,孔谈到石刻题名之类话题,任日新若有所思,拿出一个普查文物的记录本,其中记有在距九仙山深处十余里的大石棚的题名碑,其中有一则为:“诸士言公弼,中立子达,壬寅四月同游。”孔凡礼不由得老夫聊发少年狂,大呼:“不虚此行!”原来“公弼”是诸士言的字。壬寅乃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年),距离熙宁八年(1075年)不过十三年。再查《苏轼文集》卷六十二《密州请皋长老疏》提到诸郎中,此公弼即诸士言无疑。如果孔凡礼不到这深山来考察,“公弼”是谁的公案,也许就永远无法揭开。因为任日新虽抄下了这个题名碑文,并不知这个题石与苏轼有何联系。大石棚太峻峭,一般人视为畏途,将来即或有路可通,也未必有人熟悉苏轼交游达到孔凡礼的程度,而去仔细考察这个题石碑文。那天,孔凡礼以七十一岁之躯,攀山越岭,的确极累极累,但心里非常愉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吃了大苦,却破解了一大谜,不由得诗兴大作。⑬
也许,鞠持正是谁,就藏在相关的地方历史典籍和金石文物里,等待历史的有缘人破解。但无论如何,苏轼与文登的这段佳话,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值得好好挖掘,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断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①《文登城市形象宣传片发布!融古今,见未来,文登“百事可乐”》大众网
②摘自北京燕山出版社《苏东坡全集》珍藏本第五册2779——2780页(原《苏东坡全集》一百五十卷尺牍)
③《苏轼文集编年笺注(诗词附)》第7册724-725页李之亮笺注巴蜀书社
④《苏东坡全集》一百五十卷尺牍
⑤山东侨报:《东坡为何称蓬莱为文登》
⑥《朱良志:论中国传统艺术哲学的“无名艺术观”》
⑦《书法网:1965年的济南,舍利塔塔基地宫挖掘出一件苏轼精美小楷作品》
⑧《苏东坡传》林语堂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第4次印刷第230页
⑨《苏轼在密州》齐鲁书社1995年9月第1版78页
⑩2020年12月21日《青岛晚报》:宋代板桥镇与东方海上丝路:空前繁荣的宋代海洋文明
⑪《苏东坡全集》第6册3140页
⑫《走向世界》2017年7月《仙境烟台》专辑第45页
⑬《三十年回顾》刘清泉编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编229页《无冕学者,苏学大家——孔凡礼苏学研究概述》作者:石钟扬
(朱德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