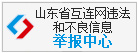忆文登中学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前后
杨岫庭

杨岫庭
1930年冬,文登中学(简称文中)一年一度招收新生的工作又要开始了。此时,我16岁,已经在私塾和“洋学堂”里读过几年书,是继续升学还是就此谋个“饭碗”,为这件事,家中发生了一场争论。
我的父亲是个忠诚老实、贫寒清苦的农民。我家每年冬春,连地瓜干也填不饱肚子,是没有条件继续读书的。那时,我们村有些青壮年人,在哈尔滨干自来水工人,我很羡慕,也想到外面去闯一闯,当个工人。但是,父母不同意,一心要把我培养成“教书先生”,认为这样比工人、农民地位高,不用种田做工,不受风吹雨打,可以守在他们身边,过平安日子。我拗不过父母,只好去考学。
结果,我被录取,进了文登中学的预科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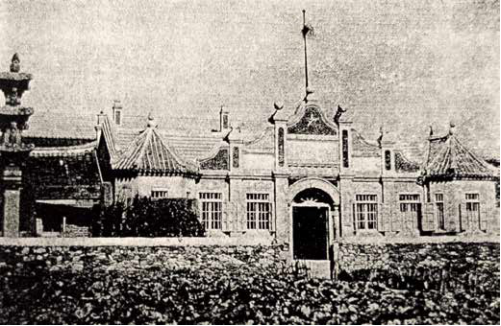
文登第一个党小组诞生地
——文登中学旧址
——文登中学旧址
1931年早春的一天,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求学之路。
文中虽然只有初中班,但在当时来说,这是文登县的“最高学府”。进了校门是个大院,迎面是新盖的课堂楼。
学校紧贴着一座大庙。那座庙,也被文中占用着。庙的东围墙开了一个便门,把大庙与文中校园连在一起。学校的办公室、宿舍、食堂都设在庙里。正殿设作礼堂,新增的两个预科班,也设在庙里。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宿舍,一看,同学们的行李差不多把通铺塞满了。正在我踌躇之际,有个细高个同学微笑着朝我走来。他接过我的行李,并帮助我安放好。我和他的铺紧挨着。
“你叫什么名字?”
“杨岫庭。”
“哪乡来的?”
“西南乡杨家疃,离这50里。你呢?”
“我叫张景芳,石岛附近人。”
张景芳比我早到一天,情况比我熟悉。接着,他领我去办理入学手续,又指点食堂在哪里,我们在哪个教室上课等。他像老大哥一样地亲热,一相识,我就从心眼里喜欢他。
连考学那次算在内,这是我第二次进文登城。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都有自己的见闻。我对什么事都感到新鲜,觉得这一下可见了大世面。但由于自己家境贫穷,衣着寒酸,总感到比别人矮三分。别的同学课余时间三五成群,或说笑谈天,或逛文登城大街,我从来不好意思加入。
张景芳家里虽然也是贫穷,衣着很朴素,但学习成绩好,待人诚恳热情,所以在同学中很有威望。他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寄托,不久我们成了莫逆之交。和张景芳一起从石岛来的,还有原道炳、盛福东、王治卿等,他们都考进了正取生八级或师范班,在学校都很出名。后来都被选进“学生自治会”。我常跟张景芳和他们在一起,并通过他们认识了师范班的邓汝奎。
我还交了一个好朋友,是同桌的于敬忠。他的家在文登城街上,父亲于泽山是救济院的书记。于敬忠家房子住不开,就在救济院睡觉。后来我搬到救济院和他作伴。张景芳等同学也经常到救济院来玩,常常谈论国家大事。有时谈到夜深了,他们干脆不回去,我们就挤着睡在一起。
我们预科班的国文教员钟平山,听说是刚从北京一个大学毕业的。他二十四五岁的年纪,个头挺高,身材细瘦,长方脸,双眼奕奕有神。此人口齿清楚,谈锋雄健,讲起课来,引人入胜。他有时讲课离开课本,讲一点新鲜事,如中国不但有国民党,还有共产党,苏联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地主、资本家倒了台,由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等等。这使很多同学听得入了迷,特别像我一样的穷学生,感到很对心思。因此,我们经常到钟老师宿舍去玩。石岛那几个同学虽然不在钟老师班上,也常和我们一起去。我们每次去,都问这问那,好像有提不完的问题。
在钟老师宿舍里,我们还认识了一个叫宋文山(后来改名叫宋澄)的人,是国民党文登县县党部的干事。不过,有时他也插进几句话,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有一次,张景芳怀着好奇的心情问:“钟老师,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钟老师微笑着说:“多看了一些书。”
我鼓起勇气说:“老师,能不能借些给我们看看?”
钟老师满口答应。从此以后,我们从钟老师那里借了很多进步书籍,有鲁迅写的,还有苏联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等等。这些作品,在我们脑海中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使我们大开了眼界。同时,要提出的问题,也随之多起来。
有一次,钟老师问我们:“你们将来还想不想读高中、读大学?”我们都说,想是想,就是家里穷,读不起。钟老师叹了一口气,说:“是啊,要是能把地主和资本家打倒,建立像苏联那样的社会就好了。”接着,钟老师给我们讲起了中国共产党,还有国共合作、国共分裂、蒋介石叛变革命等问题。他还特别兴奋地告诉我们,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已经建立了江西苏区,还要在全中国建立像苏联那样的社会。听着钟老师这些讲述,我们的心里都向往着共产党,向往着革命。
这年暑假前,预科班举行一次考试。我和张景芳等几个朋友提前升入九级,成了文中的正式学生。钟老师也不再教预科班,改教九级、八级和师范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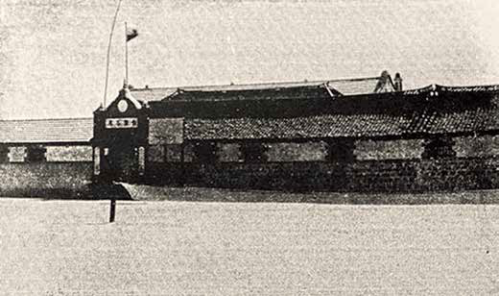
文登第一个党小组诞生地
——文登中学操场一角旧址
——文登中学操场一角旧址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凑在一起闲扯。我谈起在学校搭不起伙,想从家里背苞米面和地瓜粉,自己起伙,又感到路远背起来有困难,起伙也有困难。因此,我越说越懊恼。张景芳一直憋着气坐在那里,这时突然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说:
“中国社会这样黑暗,我们青年人要有前途,非干共产党不可!我是横了心要干共产党,你们怎么样?”他的这些话,像在干柴堆上放了一把火,顿时把大伙的激情燃烧起来了。我心里激动得怦怦直跳。接着,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看样子,钟老师准是共产党员,我们找他去!”
第二天晚上我们去找钟老师。一进屋,钟老师就看出我们几个青年的情绪今天不同往常。
“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钟老师笑着问。
大家都把目光落在张景芳脸上,因为我们事前约定让他先开口的。
这时张景芳显得有点紧张,但还是鼓起了勇气,说:“钟老师,我们想求你一件事!”“别激动,慢慢说。什么事?”钟老师亲切地说。张景芳却急不可耐,冲口而出,“我们想参加共产党,求你给介绍介绍!”钟老师爽朗地笑了,但他很快就压低了嗓门。我急忙问他:“老师,景芳说的不对吗?共产党不好吗?”钟老师望着我们,微笑着,小声说:“共产党好啊!可是蒋介石容不得共产党,他背叛革命后,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屠杀政策,逼得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我早想参加共产党,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呢!”我们几个都傻了眼。
“你不是说有苏区吗?我们到苏区找红军去,或者想办法到苏联去。”
我们都睁大眼睛盯着钟老师,指望他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钟老师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真没想到干共产党还这么难,我们的情绪有些低落了。
过了一会儿,钟老师见大家有点泄气,就笑着鼓励我们说:“别灰心!只要我们多干共产党主张的事,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好,我想总会找到的。说不定文登就有共产党人,我们不知道他,他对我们干的事清楚,到时候也许会来找我们。这就要看我们的决心了。”
这盏灯经钟老师这么一拨,顿时又在我们心中亮起来了。
张景芳又代表我们,再三对钟老师说,如果他找到共产党,一定要带着我们去参加。钟老师连连点头,说:“好!好!”当我们站起来要告辞时,钟老师又把我们留下,问我们这事跟别人说过没有。知道我们没向别人说过以后,他既严肃而又亲切地嘱咐我们,要提高警惕,要注意安全,不要不看环境,不看对象,随便乱说,以免发生危险。
从那以后,我们每次到钟老师那里去,总是怀着一种特别的心情。在钟老师那里,还常常碰到宋文山。他在那里很随便,好像比我们与钟老师的关系更亲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文中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同全国的爱国同胞一样,义愤填膺。在全校师生举行的抗日大会上,钟平山老师发表讲演,严厉谴责和无情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博得了大家的热烈鼓掌;张景芳、原道炳他们领导的学生自治会,也发起成立了“抗日义勇队”。接着,同学们都做了一色的制服,学校增加了军事训练科目。
这次大会之后不久,一天,张景芳找我,说他要参加共产党了。我急切地问:“找到啦?”他却反问我:“你参加不参加?”我又惊又喜,急忙说,“参加!”他高兴地一把拉住我的手,我也用劲攥着他的手。这时,他告诉我,并没有找到共产党,是钟老师跟他们几个人商量,为了发动抗日,搞好宣传,先成立一个组织,干共产党的事。“闹了半天,还不是共产党!”我有些着急。张景芳介绍说:“咱们有了组织,先干共产党的事,还不就是共产党?不过没有找到以前,还不能叫共产党,先叫‘三一学社’。”接着他又告诉我,眼下“三一学社”就要展开活动,揭露蒋介石的卖国反共政策,宣传共产党如何救中国,救穷人,还要宣传苏联的局势。
寒假前夕的一天,张景芳告诉我当天夜里有重要活动。天黑以后,我按照事先的约定,去到操场上,看到同学们三三两两地陆续到来。过了一会儿,大家又都结伴走开了,隐没在夜色之中。我正等得心急,张景芳拿着一个纸盒来到我面前,告诉我今天晚上分组贴反蒋标语,我们俩一块行动。他从怀里拿出一卷纸交给我,我展开一看,大约有五六寸长,二寸来宽,也有几张大一点的。我生平第一次为党干事,激动的心像要跳出口,那个高兴劲儿是没法用言词来形容的。
我们两个摸着黑,悄悄地从操场后面转到大街上。街上一片漆黑,也很少有人行走。来到分给我们的地段,张景芳端着纸盒刷糨糊,我把一张张标语贴到墙上去。
第二天天刚亮,小小的文登城轰动起来了!一张张“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的红绿标语,犹如一把把利剑,刺痛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达官贵人;又恰似一把把火炬,使人民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人们争相传说着,简直把贴标语的人看作是天兵天将。是啊,不但大街小巷,就连国民党县党部的大院里,也贴上了标语(我后来知道,是宋文山贴的),这能不使人惊讶吗?
文登城里这一声春雷,很快传到了远近乡下。人们心中的爱国热情都给点燃起来了。
正在我们兴高采烈,悄悄地欢庆胜利的时候,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我们尊敬爱戴的钟平山老师,接到了校方的辞退通知。
“三一学社”经过研究,决定用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出面,以钟老师教学有方为理由,同校方交涉,要求校方收回辞退通知。但是,校方坚决不同意,说钟老师在“九一八”事变后,太出头惹眼了,如留下来,对学校和他本人都没有好处。
我们着急地去问钟老师怎么办,钟老师亲切地说:“离开学校,看来势在必然。我走了,组织还在。以后你们有事,去找宋文山,他可以帮助你们。我不会忘记你们,等找到了党,我就写信来。”
放寒假的头一天,我们怀着忧伤惜别的心情,送钟平山老师踏上新的征途。寒假后回校的第三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晚上到西关小学开重要会议。好不容易等到晚上,我和张景芳、于敬忠、邓汝奎等一起来到约定地点。西关小学的教员张孟浪,文中的王治卿、盛福东等人,已经先一步到了。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个人。今天大家的神情都显得异常庄重、严肃,见面时只是默默地点点头打招呼,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原道炳陪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走进屋里。这个人细高个,衣着比较讲究,头戴礼帽,身穿棉袍大褂,脚上穿着皮鞋。见到这个陌生人,我们即刻感觉到,他大概就是我们要等的人了。我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用尊敬而又带几分惊异的目光看着他。
来人带着亲切的微笑,用明亮的眼睛环视了一下屋里的人,客气地示意大家坐下。他也很自然地坐下,好像回到亲人之中。
原道炳以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向我们介绍说:“这是省立七乡师(即文登乡师)校长于云亭先生,他带来了钟老师给我们的信!”

于云亭
一听说钟老师来了信,群情振奋。我们彼此用眼光交流着欣喜之情,相互庆幸着。接着,原道炳把钟老师的信读了一遍。信的大意是:我们这一批青年学生,革命热情很高,在此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更应团结奋斗。因为种种原因,他不能同我们在一起了。现在,他的好友于云亭即将到文登乡师任校长,他已向于先生详细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于先生表示很愿意指导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很好地接受于先生的指导。
原道炳读完了信,就请于云亭讲话。他说:“同学们的情况,钟先生都对我说了,有些事信上不便写。大家一直在急盼盼地找党,我今天就是来介绍你们参加共产党的!钟老师和你们一起组织的‘三一学社’已经接受了党的初步考验,从现在起改为党的一个支部,原领导人就是党支部的领导成员。”
啊,我们入党了,还有了党的支部!在这个春寒料峭的夜里,人人心里恰如燃起一团火。我们多想痛痛快快地高呼几声“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是,情况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接着,于云亭又给我们讲了党的组织纪律及以后党员之间相互联系应注意的事项等。最后他还提出,为了在新开办的文登乡师开展党的工作,要文中去几个党员投考乡师,作为发展乡师党组织的基础(后来听说去了4个党员)。
文中党支部成立不久,在国民党县党部工作的宋文山到北平去了。
当时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胡建民到济南去,报告文中有共产党的组织,反蒋标语也是文中学生贴的。文中党支部得到这个消息后,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局势,研究了应付措施。当时山东的“太上皇”、大军阀韩复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一心抵制蒋介石的势力打进山东;胶东的土霸王、军阀刘珍年,不但抵制蒋介石,还提防着韩复榘;文登的县长刘昶年是刘珍年的亲信,与县党部有矛盾,他既不喜欢学生闹事,又担心县党部借镇压学生之机扩大势力;县党部虽然对学生的反蒋活动很恼火,但他在文登没有基础组织,只是个空架子;文中校方不太干涉学生的活动,但胆小怕事,为了维护学校和自身利益,偏袒学生;学校党支部建立后,党员积极性很高,学生自治会、抗日义勇队又都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特别是全国抗日的呼声很高,学生有坚强的后盾。因此,党支部决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趁胡建民刚从济南回来,来个先发制人,给他一个“下马威”。
在文中党支部领导下,学生自治会出面召开全校同学大会,揭露了胡建民到济南诬告文中,陷害全体同学的卑劣行为。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了,人们挥舞着愤怒的拳头高呼:“跟胡建民论理去!”“找胡建民算账去!”“要胡建民交出证据来!”
自治会主席当即宣布:“换上制服,上街游行示威,到县党部找胡建民算账!”
不一会儿,群情愤怒的学生队伍浩浩荡荡地涌上了文登城的街道。“打倒国民党书记长胡建民!”“我们要抗日!”震天的口号声如滚滚春雷,在蓝天白云间激荡,山城文登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壮举。沿途的老百姓热情地议论着,并用惊讶不已的目光,看着这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
我们来到县党部门口,列队摆好了阵势,就派代表进去交涉。胡建民不在,自治会几个领导人研究之后决定,派一部分人留在这里监视,大队回到学校。
当天下午,留下监视的同学,把胡建民抓到学校里来了。消息传开,同学们蜂拥而至,把胡建民团团围困在改作礼堂的大殿里。堂堂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如今满头大汗,一副狼狈相。他结结巴巴,一口一个“兄弟我”至于那后面还说了些什么,被同学们愤怒的口号声、质问声盖过了,谁也听不清。我们质问了他个把小时,他吓得浑身发抖,有几次差一点瘫坐在地上。后来,学生自治会决定,把他拉出去游街。一声令下,他像死猪一样被同学们推拥着押出了校门。
文登县长刘昶年,恨不能大刹一下胡建民的威风,削弱蒋介石和韩复榘在文登的势力,巩固他刘家的地盘,所以一直没有出面干涉。直到下午,他听说胡建民被抓到文中,担心再不出面,以后不好说话,又怕火烧到县政府头上,这才匆匆忙忙带着护兵向文中赶来,正巧,和押着胡建民的队伍相遇。他和护兵手拉手拦住了我们的队伍,向我们喊话:“同学们,不能这样。你们先回去,本县长保证把这件事处理好,让你们满意。”
就趁这个机会,胡建民溜跑了。
这次斗争取得的初步胜利,使同学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也为文登城的老百姓出了一口气,街谈巷议,都夸学生们有胆量。
党支部决定,乘胜前进!紧接着又组织了一次全校同学的大游行。这次游行讲明了策略,所喊口号,只针对胡建民个人,这样既可以避免给敌人留下口实,又可以加深县政府与县党部之间的矛盾。同时,又派出学生代表,多方进行交涉。不多几天,国民党文登县党部的正副书记长都调走了。当然,这个结局,一方面是学生们在党领导下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各地方派系之间“狗咬狗”的斗争,也从反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国民党文登县党部,一直是关门大吉。
就在我们兴高采烈暗暗庆祝这次斗争胜利的时候,教育局突然把文中的校长、训育主任和教务长三人调走了。紧接着,又传来一个消息,刘珍年认为文登局势不稳,要派骑兵团来文登驻防。这突如其来的一连串变化,使大家心中非常不安。党支部研究决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一部分身份比较公开的党员离开学校,党支部由平时不大露面的同志负责,继续与于云亭联系。我的好朋友张景芳和石岛的几个同学,决定转赴北平,去找钟平山老师和宋文山。我继续留下。
不多久,刘珍年派的骑兵团到了文登。文中派来的新校长是个国民党员,对学生控制很严。我和于敬忠在救济院住的房子,也被骑兵团抢占,我们只好搬到双茂客栈去住。

文登第一个党小组诞生地
——文登中学图书馆旧址
——文登中学图书馆旧址
我在学校也是活动“红”了的,已经引起校方的严密注意,加上家里经济拮据,实在无力再供我读书,所以在1932年寒假,我也不得不离开学校。
尽管以后的斗争十分艰苦,但党在文中播下的革命种子,在马列主义春雨的浇灌下,终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当然,斗争是复杂的,人们的变化也是很大的。但是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文中第一个党支部的绝大多数党员,戎马一生,金戈南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更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杨岫庭(1914年—1990年),男,山东省文登县(现威海市文登区)杨家疃村人。1931年1月加入共产党。1934年任中共文登县委书记。1938年2月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1940年3月任东海独立团五营营长。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文登境内与日伪顽军数十次战斗,如青石岭战斗、崮头战斗等,立下赫赫战功。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后勤运输团团长、第九纵队后勤部第二运输处处长等职。1957年2月转地方工作,历任南京化工公司磷肥厂副书记兼副厂长、化工部第八建设公司副经理、南京化工公司化工机械厂副厂长等职。1983年2月离休。1990年10月病逝于南京。
(来源:中共威海市委党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