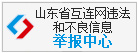出生于1925年的荣成籍抗战老同志唐文杰,曾参加胶东军区民运队,跟着胶东军区主力部队转战胶东、潍坊多地,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为牺牲战友整运遗体等,同时也见证了祖国从弱到强、越来越强大的过程。

以下为其口述个人部分抗战经历。
32个民运队女兵牺牲了25人
1944年抗战后期那会儿,我才18岁,我二姐在威海的八路军武工队当教导员。她说:“四妹,你打小儿嘴巴就会说,来咱们胶东军区民运队吧,用嘴也能打鬼子!”于是,我就成了胶东军区民运队年纪最小的女兵,一直战斗在莱阳、黄县(龙口)、蓬莱、掖县(莱州)一带。
我们没有发枪炮子弹,对付敌伪军的家伙什儿,就是嘴皮子、浆糊桶、快板儿,还有铁皮卷的大喇叭。干啥?专往敌人心窝子里扎——到据点外头喊话、贴标语、唱小戏,找伪军家属拉家常……让他们知道,给鬼子卖命没出路!
记得大约是秋天,天都擦黑了。我和另外仨姐妹,来到一个离敌人炮楼200米远的农家院。那炮楼黑黢黢的,像吃人的怪兽。村里的老少爷们早帮我们探好路,几个壮实的男同志蹲在墙根下,肩膀就是我们的梯子。踩着他们,我们几个轻手轻脚爬上了那低矮的土房顶。
趴好,掏出铁皮喇叭。炮楼顶上哨兵的影子都看得清。我把喇叭口对准那边,开始喊,声音又脆又亮,穿透黑夜:“王占魁,知道你老娘病了吗?她天天盼着你回家!”“李二狗,鬼子拿你当枪使,打的是咱中国人!”
我们喊的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据点里那点事,我们门儿清!这些话,句句都像小刀子,专往他们心肝上戳。
炮楼里登时就乱了。没多会儿,那歪把子机枪就响了!“哒哒哒哒……”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打在房檐上,“噗噗”地冒土烟。我们早有经验,赶紧一缩脖子,身子紧紧贴在房檐侧面的旮旯里。那子弹,听着近,其实只要趴得够低、藏得够巧,一时半会儿打不着。
等他们枪声一停,喘口气,我们几个眼神一对,立刻猫着腰,踩着下面战友的肩膀,飞快地溜下房顶,换个院子,再爬上去接着喊,就这么跟他们耗上了。他们打,我们躲;他们停,我们喊。寂静的夜里,就听到我们几个姑娘的声音,还有那恼羞成怒的枪声来回地响。炮楼里的敌人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有没有埋伏,缩在“乌龟壳”里,愣是不敢出来追。
那天晚上,我们喊了有一个多钟头,嗓子都冒烟了,眼看任务就要完成,突然,在我趴着的隔壁房顶上,敌人的机枪像疯了一样扫过来!我听见两声短促的惊呼,然后再也没了动静。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冰窟窿里。
撤下来才知道,下午还跟我手拉手说“等革命胜利了要一起去学堂念书”的两个姐妹,就在我旁边不远的那片房顶上被敌人机枪打中了,没能救回来。
我们那批民运队的女兵,刚入伍时,是32个胶东姐妹,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天,就剩7个了。
那房顶,那铁皮喇叭,那夜里嗖嗖飞过的子弹,还有姐妹们倒下去时年轻的脸。80年了,我闭上眼,还在眼前晃,忘不了,也不敢忘。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是她们拿命换来的。
12岁孩子为掩护我们被子弹打穿手掌
我至今还记得1944年那个刺骨的冬天。18岁的我,跟着侦察队长丁光在潍坊的敌占区活动。那天,我俩扮作逃荒的父女,顶着北风,踩着冻得梆硬的土路,悄悄摸进了一个被伪军控制的村子。
天完全黑透后,我们找到一户可靠的养羊人家。刚进屋,外头突然响起一阵狗叫,紧接着就是“砰砰”的砸门声。
“开门!搜查!”伪军在外头扯着嗓子吼。
我心头一紧,看见房东家的小栓子贴在门缝上往外看。这孩子才12岁,瘦得跟豆芽菜似的,可眼神特别镇定。他转过头,压低声音说:“快!反穿羊皮袄!从后窗走!”
老丁反应快,抓起炕上那两件带着羊膻味的皮袄就往身上套。那皮袄又厚又重,羊毛扎得脖子生疼。我们刚翻出后窗,前门就被砸开了。
我听见小栓子在外头喊:“后面是羊圈!只有羊!”接着就是“哗啦”一声,老丁撞开了羊圈栅栏。受惊的羊群“咩咩”叫着往外冲,我俩混在羊群里,借着夜色往外跑。
“砰砰砰”——身后响起枪声。突然听见小栓子“啊”地一声,我的心猛地揪了起来。后来才知道,是本村一个反动地主向敌人告密。那孩子为了掩护我们,硬是用身子堵着门,手掌被子弹打穿了。
等敌人追出来时,我俩早就跟着羊群跑远了。子弹打在冻土上“噗噗”直响,可打不着我们。那件羊皮袄救了我俩的命。
三天后,老丁带领武工队,除掉了告密的地主。现在想起来,小栓子那孩子真是好样的。要不是他忍着剧痛堵着门,我和老丁怕是早就……唉,这些事啊,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那些永远睡在白布袋里的好战友
1945年春,我们民运队跟着胶东军区主力部队16团在胶东、潍坊东部转战,我作为民运队女兵,除了喊话演戏,顶要紧的,就是用白细布制作的“遗体袋”,把牺牲的战友体体面面地送回家。
仗一停,硝烟还没散,我们就得上去。含着泪,忍着心尖上的疼,给牺牲的同志擦净脸,理好军装,整得就像睡着了一样,再轻轻放进这白布袋里,抬上担架,一步一步,送他们回后方的青山安眠。
有一回战斗,炮打得激烈,天都震红了!我们几个姐妹,贴着地皮往前爬,得把伤员抢下来!老兵教过我们保命的法子:炮弹刚炸开的坑,就是下一炮打不着的地儿。得瞅准了,一个坑接一个坑地往前挪。
我前头是个刚分来的小姑娘,脸白得像纸。敌人那炮,追着我们的脚后跟砸!她大概是吓坏了,瘫在那个刚炸开的弹坑里,怎么也挪不到下一个坑去。眼瞅着敌人的炮弹往这边落。
不能扔下她!我啥也顾不上了,顶着那嗖嗖乱飞的弹片和溅起的泥块,拼命爬到她身边。抓住她胳膊想往外拖。可我这身子骨太单薄,她整个人软成了一摊泥,死沉死沉。我怎么也拖不动她,就在那要命的当口,头顶上炮弹撕开风的声音传来,我下意识使出全身力气往旁边一滚。
轰!我耳朵里嗡的一声,啥也听不见了,眼前一黑。等苏醒过来,嘴里全是土腥味和硝烟味,耳朵里嗡嗡响。甩甩头,挣扎着往前一看,我趴着的那个坑,空了,她只剩下半截身子,那件新发的灰布军装被血浸透了,辫子也只剩了半截……
我抹了把眼泪,不顾手臂上的伤口,继续往前爬。不能停!前头还有倒下的战友等我!
等仗打完了,我摸索着回来。把她放进白布袋子,让她安眠。
连着十几天夜里,一闭眼就是那炮响,就是那新发军装上浸透的血,还有那半截乌黑的辫子……
今天的好日子,都是我这些倒下的同龄人——那些永远睡在白布袋子里的好战友,用命铺出来的。我这心里,疼了一辈子,也记了一辈子。(于迎雨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