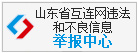第四章 岁月深处
殷红的情思
天刚破晓的时候,雪停了,吼了一夜的北风也终于变了调,吁吁地喘着,声音疲惫,含含糊糊。
这一宿,矫月志睡得很不踏实。也难怪,一想到儿子今日完婚,她便像打了鸡血似的,心底泛起隐隐躁动。毫无疑问,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因为,捱过三年困难时期,新人的结合使田家老宅又重新萌发出春天的憧憬。
吃过早饭,大儿子田瑞荣推起借来的自行车,兴冲冲地出门了。双胞胎妹妹叽叽喳喳跟到胡同里,亢奋的眸子喜气洋洋,就像随时都会燃响的烟花爆竹。“安(儿子小名)啊,路上小心点。”母亲的声音从院里撵出来,“糙的地方,就下来,推着走,可千万不敢摔着新媳妇。”儿子认真地点点头,刚露脸的朝阳在他额上涂了光,油漆一般,亮汪汪的。望着儿子远去的背影,母亲的目光渐渐有些恍惚,神情痴痴地,就像望着一个真实的梦境。是的,透过记忆的景深,她看见二十五年前的旭日又开始故地重游。哦,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她满脸羞涩地走进小院,成了村民田宝松的媳妇。转瞬间,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年轻的媳妇熬成了婆。回首前尘,时光潺潺倒流,往事历历在目。
矫月志的娘家是牟平县前垂柳村。她1916年8月出生,是矫家长女。及笄之年,母亲病逝。不久,父亲再婚。从生育的角度看,后妈的确是一块适合耕作的膏腴之地。丈夫刚一沾身,她就立马开怀,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噼里啪啦”,生生不息,短短几年工夫,就给矫月志添出了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这一来,矫月志可就惨了。从早到晚,她像热锅上的蚂蚁忙得团团乱转,放下这样,拾起那样,直累得东倒西歪,筋疲力尽。咳,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啥?生活所迫,只能硬着头皮,勉力为之。实际上,即便与后妈没有感情方面的弯弯绕,单就家中排行而言,身为老大,她要承担的重任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二十四岁,矫月志才谈婚论嫁。夫婿并不是她自己选的。丈夫比她小一岁,属蛇。夫妻一照面,矫月志心头一震:妈呀,男人面黄肌瘦,病歪歪的。不知为什么,他怄气似的拧着眉头,好半天不吭气。新娘子惘然无措,只好绷着身子,很不自在地坐在炕沿上,神情显得颇为尴尬。过了一会儿,又偷偷朝男人瞥了一眼,心想,不会有啥毛病吧。怕什么偏偏来什么,没过多久,她就认定,丈夫的脾胃的确有问题。看上去,饭量算是马马虎虎,可一拎锄镢,便筋骨疲软,有气无力。那软塌塌的样子让人好生纳闷:一日三餐都吃到什么地方去了?事情明摆着,丈夫不给力,做媳妇的只好能者多劳,用今天的话说,她必须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汉子。对此,母亲的安慰只能是那句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对女儿来说,看似简简单单一个“随”字,包藏了多少郁闷,多少委屈,然而,事已至此,有啥法子?
就这样,在没完没了的操劳中,日子没滋没味地过下来了。
现在,儿子像她当年一样,满怀期待地走进婚姻。她不知道儿子和媳妇将来日子过得怎么样。不过,凭着半生的经验,她认为,一个贤惠的儿媳就是对家族的最大成全,而这种成全无法祈求,只能听凭运气。
大约两个时辰后,翘首以盼的自行车终于出现了。会心的笑容发面似的膨胀开来,把两眼挤成一条缝。不一会儿,橘黄色的火苗便探头探脑溜出灶口,袅袅升起的炊烟也一改往日的寡淡,变得香气氤氲。不经意间,夕阳从烟囱上悄悄滑落,调皮的星星则好奇地倚住新人的窗户。月亮笑盈盈地嘘了口气,月光便蹑手蹑脚地溜到闺房中去了。这个夜晚无疑是属于新郎和新娘的,当然,也是属于矫月志的。说实话,有生以来,她从未像今晚这样心绪复杂,百味杂陈。昏暗中,丈夫鼾声阵阵,这个当了公爹的男人用响亮的鼻音酣畅地抒发着滞留在心中的欢喜。朦胧的月光雾一样在枕边流淌,她静静地瞅着屋顶,目不交睫,没有丁点儿睡意。“冬明到底在哪儿呢?”她在心里默默念叨,“这么多年了,也不给妈来个信,这孩子,不知道妈一直惦记着你吗?”过了一会儿,她把视线缓缓移向窗棂。窗外,夜幕低垂,月色迷离。忽然,她发现一个隐约的光点闪闪烁烁。她定住眼神儿,只见记忆的流萤从时间幽谷中悄无声息地飞出来,渐渐地,昨天的荧光越来越亮了。
于是,在自家逼仄的小院里,她与二十多年前的新媳妇不期而遇。
过门一年后,大儿子出生了。
人说女大十八变,实际上,女人的最后一变是做了母亲才得以完成的。就在鼓胀的肚皮骤然凹陷的一瞬间,她突然明白了什么叫牵肠挂肚。由于奶水不足,那稚嫩的哭声鞭子一样把她抽得遍体鳞伤,尽管如此,丈夫依然笃信多子多福。转过年来,土炕上又添出一个男婴。没承想,小家伙时乖运蹇,啼哭了数月之后,便再也没了动静。就在这时,胶东育儿所由东凤凰崖村转移至田家村。根据农会的安排,保育股股长孙亚东带着尚未断奶的儿子冬明住进田家老宅的东屋。这是一个改变故事走向的突发情节,矫月志看到,一缕新鲜的阳光从新房客的眼中溢出。接下来,他用满嘴新词对房东夫妇进行了第一次人生启蒙。矫月志忽然意识到,生活原来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那一刻,成为她生命节气中的惊蜇;那一刻,沉睡在心底的希冀悄然苏醒。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孙亚东,眸子亮亮的,那是景物的反光,真的,她看见孙股长描摹的愿景在春光里尽情铺展,草长莺飞,柳绿花红,这个梦太奇妙,也太迷人了。正由于此,当孙亚东把饥肠辘辘的小冬明递过来时,她不假思索地把小家伙抱在怀里,会心地笑了,那意思是说:把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胶东育儿所所在地田家村
就在矫月志精心哺育冬明的三年中,胶东抗日根据地的版图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开始酝酿共和国的蓝图。继冬明之后,育儿所又送来一个叫“生”的女娃。奶了九个多月,被父母领走。待到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从北京城的西北方向踏过旧称“中官屯”的地方,向着十四公里外的天安门广场挺近时,矫月志的第三个孩子已经半岁了。
刚解放那会儿,心情好舒畅啊。瞧,天是那么蓝,就像刚刚洗过的蓝绸子,好滋润,好养眼。她觉得,心里亮堂极了,整个心房就像用玻璃做成的一样。日后回忆起来,那的确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不仅仅因为年轻,更因为那是一个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年代,豪迈而且浪漫。所以,当村支书掰着指头历数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时,她觉得,那粗粝的嗓音如同草丛里惊飞一只野鸡,让人听得格外兴奋。
“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支书在台上眉飞色舞,她在台下如醉如痴。
“那……不用油用啥呢?”有人冷不丁冒出一句。支书一愣,人们哄地笑了。
“用电。”
“电?电是啥玩意儿?”
支书搔搔后脑勺:“电……就是电嘛。”他很谦虚地挥了挥手,显然,余下的问题要靠提问者自己去解决了。
电灯?这东西到底是啥模样呢?她想啊想,越琢磨,那不用油的电灯就显得越神秘,久而久之,那神秘就变成一种怂恿,一种每每使人心驰神往的蛊惑了。
然而,岁月之河一路奔放却又蜿蜒曲折。当阳光洒满山川的时候,风雨也会不期而至。随后的一段经历让当事人始终无法淡忘,时至今日,矫月志的子女依然对困难时期所感受到的母爱记忆犹新。
在老三田瑞夫的描述中,挨饿的滋味好难受啊!那段日子,身上的每个部位都张着饥饿的嘴巴,每颗牙齿都蓄满了撕咬任何东西的冲动。一天到晚,近乎虚脱的烧灼感如影随形,没完没了地纠缠着他,也折磨着他。那是一个可怕的梦魇:发自身体内部的坍塌声让小男孩深切体验了关于人类生存最原始的恐惧。他说:“那几年,每次吃饭,老妈都是先尽着我爸和几个孩子上桌,她自己饿肚子是常有的事。”
不知不觉中,孩子们的饭量越来越大,而母亲的饭量越来越小,奇怪的是,她的胳膊呀,腿呀,却一天天地粗起来,皮肤也变得隐约透明,好像蒙了一泓水,亮汪汪的。小女儿瑞玲傻乎乎地问:“妈,你吃的比我还少,咋就胖了?”母亲的嘴角泛出一缕苦涩的微笑:“傻闺女,这哪是胖了!”说着,提起裤脚,拇指在脚踝上方轻轻一按,顿时,皮下的肌肉融化了似的,显出一个深深的凹陷。呀,怎么会这样?母亲的解释轻描淡写:“水肿了,没事。”女儿怯怯地望着母亲,眸子里现出一种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忧郁。从那天起,她突然变得懂事了。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盼来了春天的消息。
一觉醒来,湿润的春风开始呢喃,荒芜的田野悄悄漫开一种潮湿的发酵似的气息。伴着春风的梳理,摇曳的柳枝显得优雅而富有节奏;山坡上,田埂边,一簇簇野花从草丛中探出脑袋,鲜嫩的花瓣绽放出簇新的娇媚。挣出了大饥馑的泥淖,面黄肌瘦的共和国又脚步踉跄地加入了春天的家族。于是,在历经三年磨难后,全世界又重新听到了一个古老民族衰弱而又倔强的心音。
忙完三夏,矫月志开始给大儿子田瑞荣张罗婚事。很快,老两口卷起铺盖,把最东头的房间让给儿子。接下来,新房的布置让人大跌眼镜:除了一盘光溜溜的土炕,小屋里只有一个老辈人遗陈至今的旧式立橱。一人多高,双门对开,颜色黑乎乎的。定睛一看,面目沧桑,神情委顿,全然一个过气的古董。什么?新房里连个“喜”字也没有?难道买张红纸也成了一种奢侈?那时候,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花,手头着实紧巴。好在新媳妇通情达理,一进门就用云淡风轻的笑容剪出一幅窗花,给清贫的生活增添了一处温馨的装饰。
没过多久,儿媳妇怀孕了。
消息一经坐实,矫月志眉开眼笑,丈夫同样美滋滋的。十个月后,积蓄已久的喜悦终于诉诸于生动的表达方式:抱起老田家第一个孙子,她不由得心花怒放,同时,也如释重负,小家伙的嘹亮哭声无异于广而告之,作为母亲也作为奶奶,她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她听来,时断时续的啼哭很有一点即兴表演的味道,于是,拥挤和嘈杂的空间里又增添了一种令人兴奋的骚动。她觉得,那响声简直就是天籁之音,真奇怪,当初拉扯几个儿女时,感觉为啥不像现在这样明显呢?
有道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刚当了奶奶没几天,小孙子就生病了。
一开始,小家伙的额头上冒出几颗疹子,针尖大小,红红的,像灶膛里偶然蹦出的火星。由于缺乏经验,年轻的妈妈并未在意。不料,没过两天,不起眼的火星就燃成燎原之势。矫月志兀自一惊:糟糕,出疹子了。她赶紧吩咐儿媳:“快,建威她妈(孙子乳名),用淘米水给孩子洗洗,再不行,找个土豆来,切成片,给他贴贴。”很快,洗也洗了,贴也贴了,火势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轰轰烈烈掠过头顶,一路烧到脊梁上去了。无以言表的瘙痒把小家伙折磨得痛苦不堪,他拼命地闹啊,哭啊,把奶奶哭得颦眉蹙頞,愁肠百结,目光哀哀地望着孙子,嘴里反复絮道着:“求求你了,老天爷,能不能行行好,让我替替他?唉,这么点儿大的孩子,不会说不会道的,让他遭这个罪,真是作孽呀!”旁边的儿媳受了感动,一双眸子泪汪汪的。她知道,婆婆的祈告发自肺腑,为了救护孙子,不惜以命换命。然而,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二十多年前,因为同样一番感慨,婆婆竟遭遇了死里逃生的可怕经历。原来,为了救治严重贫血的生儿,矫月志曾一次次地挽起袖子。而且,因为遵从保密的铁律,那一管管砖红色的血液始终悄无声息地锁在记忆的仓库里。直到有一天,情感密档终于解封,人们方才知晓,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亲情故事,一段感天动地的母爱传奇!
生儿刚来的时候出生不过四十多天,精神萎靡,面色枯黄。不知为什么,与同样大小的孩子相比,小丫头的感知能力存在明显落差。譬如:看到移动的物体,目光跟踪迟缓,总是慢上半拍;再譬如,抚摸她的小脸、小手,反应亦不明显。不仅如此,还老爱哭闹,动辄哼哼唧唧,憋得小脸通红;有时候,睡着睡着,忽然胳膊一抖,引发全身惊厥般的悸动。矫月志为此惴惴不安,精心喂养了一段时间,情况未见任何改善,她一脸愧疚地对丈夫说:“孩子的爹娘在前线打鬼子,把命都豁出去了。咱连个孩子都看不好,咋对得起人家呀?”说罢,果断抱起生儿,气喘吁吁地找到医务组。经过诊断,生儿患有严重的贫血症。矫月志赶忙询问:“咋个治法?”大夫两手一摊,无奈地说:“这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瞒你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治疗的药物。”矫月志当场傻眼了,一迭声地呻唤道:“妈呀,这可咋整?这可咋整?”大夫的嘴角泛出一丝苦涩:“现在看,唯一的办法只能给孩子输血了。”矫月志顿时笑逐颜开:“输血?这还不简单!”她撸起袖子把胳膊往大夫眼前一伸,“抽吧,咱有的是。”看到矫月志神情恳切,大夫连忙解释:“先别急,你的血能不能用,得先化验一下,看看是啥血型。”不一会儿,答案揭晓了,大夫满意地点点头。慎重起见,大夫决定先输二十毫升,观察一下孩子身体有何反应。很快,鲜红的血液顺着胶管缓缓流入生儿的体内,矫月志目不转睛地盯着孩子,静谧中,她隐约听到了生命的潮汐在悄悄涌动。然而,一个时辰过后,她的眉头慢慢蹙起来,眼里的光渐渐暗下去。唉,生儿没有丁点儿变化,依然像往常一样哭闹不止。第二天一早,她就抱着孩子去医务组当面陈情:“昨儿输了血没管用,我寻思着,是不是输得太少了?今儿就多输点吧!”念其救子心切,医生同意了她的请求。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一直延续到第八天,殷切期盼的好消息终于姗姗来迟——黄表纸一样的小脸蛋儿泛出隐约的胭脂色,到了夜里,小家伙也比从前睡得踏实。矫月志喜上眉梢,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不料,再去抽血时,大夫的脑袋摇得就像拨浪鼓:“不行,不行,这么个弄法谁受得了?搞不好,会出事的。”说着,目光严肃地望着矫月志:“你回去照照镜子,真的,脸色好难看哩!”矫月志认真辩解:“哪有你说得那么邪乎,我能吃能喝,好着呢!”大夫依然不为所动:“你先养养吧,等过些日子再合计。”矫月志一听,急了:“那得等到啥时候?生儿现在刚见好,要是不接着治,前几天输的血可就白瞎了!”说话间,一个村民慌里慌张跑进来,“大夫,我老妈肚子坏了,疼得要命,麻烦你去瞅瞅吧。”大夫转身背起药箱,匆匆走了。待到出诊归来,发现矫月志依然默默地坐在那儿。大夫一声长叹:“你这个人,真犟啊!”
于是,一切照旧。
也正是从那天起,她的脑瓜开始发木,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记得稀里糊涂。说不准是第十天还是第十一天,果不其然,出事了。那天输完了血,矫月志的意识变得恍恍惚惚的。她闹不清楚,究竟是自己摇摇晃晃往前面走,还是胡同歪歪扭扭朝脚下爬。刚拐出巷口,突然两腿发软,身子踉跄,脚下的地面变得不真实,仿佛踩到棉堆上。她慌忙揽紧生儿,倚着墙根歇了好一会儿,才双脚闪跌着踅回老屋。爬上黑黢黢的土炕,眩晕反倒更严重了,身子悠悠晃晃,仿佛浸在水里,慢慢地,沉下去,沉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意识的链条彻底断开了。
昏睡了一天一夜之后,她终于醒了。
“醒了,总算醒了!”声音很遥远,喑哑中透着惊喜。矫月志眼睛吃力地睁了一下,随即,她看到了一张模糊的脸,丈夫的感喟哆里哆嗦:“哎哟,吓死我了。”
单凭这句话,这个早晨就绝无仅有。
没错,就在视线清晰的一瞬间,丈夫的满眼血丝让她重新认识了这个相伴已久的男人。有生以来,她头一次意识到,有时候,比女人心理更脆弱,其实是老爷们羞于公开的秘密。“生儿……”一缕游丝般的呻吟从嗓子眼里挣出来,若有若无,丈夫赶紧扶她坐起来,噢,小丫头正在美美地酣睡哩。已然滋润的小脸蛋儿像胀满了汁液的小甜瓜,粉嘟嘟,水灵灵的。那一刻,她惊奇地发现,看似平淡的生活原来那么美好,她感到了一种失而复得的欣喜。
第二天,生活便恢复了先前的模样——她又开始在灶台前忙碌,在井台上浆洗,在灯影下缝补。很快,粗糙的手背又皲裂了,深深浅浅的口子绽出嫩肉,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张着小嘴。她像往常一样,抹上些许唾沫,再涂上一层草灰。一周后,她又抱着生儿去了医务室。
干啥?大夫疑惑地盯着她。
嘁,明知故问,输血嘛!
母爱真是具有不可思议的功效啊!在它的疗愈下,生儿奇迹般地康复了。
谈及往事,儿子田瑞夫补充了这样一个细节,他说:“那一年,家里的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输了那么多血,身体很虚弱,老爸的病情也加重了。家里光有开销,没有进项,这日子可咋过?那段时间,可把老妈愁坏了。为了给老爸治病,她狠狠心,先是卖了干活的小毛驴,又卖了家里的两亩地。现在想想,能对付着熬过来,真是不容易。”
在由乳山市党史办和乳山市档案局联合编著的《胶东育儿所》一书中,有一段口述记录于1984年11月2日。
我们是崖子镇田家村田宝松、矫月志夫妇,胶东育儿所保育股股长孙亚东曾在我们家住过,孙亚东的男孩叫“东明”,是我们给他看的。后来又奶了一个孩子叫“生”,是王桂芝奶养的小军的妹妹,她的母亲叫房玉真,奶到八九个月被领走了。
……
渐渐地,岁月荏苒,她觉察到自己的腿脚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灵便,她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
老了,真的老了。
岁月用深深的皱纹在她的额头刻出了沧桑,也刻出了坚忍。
她像一根汁液饱满的甘蔗,被生活的牙齿嚼呀嚼,嚼了几十年,结果,嚼成了一撮渣子。现在,她的面孔已经找不到年轻时的丁点儿痕迹——微蹙的眉峰下,清澈的眸子变得浑浊,秀美的腰肢已经佝偻,走起路来,步履也明显迟缓了。天气晴好的时候,她会慢腾腾地走进小院,默默坐在一个不碍事的角落里,呆呆地愣神儿。明晃晃的日光水一样漫过来,浸着她干枯的面容,也浸着她花白的头发。苍老的目光虚虚地瞄着某个地方,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时间长了,家人见怪不怪,以为是衰老的结果。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老人此刻正在思念的围城里绕来绕去,为找不到出口而苦恼。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动人场景。
瞧,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春草绿,她倚在门前,凝眸眺望。孩啊,这么些年了,咋不给娘捎个信呢?
光阴荏苒,又是一年秋叶黄,她枯坐树下,喃喃絮叨,孩啊,你现在身体咋样?日子过得还好吧?
面对亲情的迷雾,她望眼欲穿,乳儿究竟在哪呢?忽然,她伤风似的拢紧衣袖,不一会儿,眸子里竟有雪花飘落了。
印象中,2000年的第一场雪下得真大。
洁白的雪花飘飘洒洒,一夜之间,就把田家村装扮成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刚吃过早饭,孩子们的欢笑声就在湛蓝的天幕下鸽哨般盘旋开了。大概是受了喧闹的怂恿,矫月志笑吟吟地走出小院。抬头一看,道边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枯木逢春,纷披的枝条上开满了耀眼的银花。再往远处瞧,整个村子像刚做完美容,厚厚的面膜遮蔽了所有丑陋,街道和房舍都变得那么干净、纯粹,真美呀。待了一会儿,转身回家。没走几步,脚底一滑,两手挓挲着撑出去,屁股着地的刹那间,右臂发出断裂的脆响,她疼得龇牙咧嘴,哎哟,胳膊不敢动了。看到母亲痛苦的样子,孩子们关切地问:“要不,去医院看看吧?”“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她显得蛮有把握,好像那胳膊是自己安排的托儿。然而,事实偏偏唱了反调。捱了十几天后,她方才醒悟,这条胳膊和自己彻底闹掰了。
“怎么现在才来?”医生指着X光片责问道:“你看看,骨折面都长出骨痂了。”大儿子惶恐地跟上一句:“现在咋治?”“耽误了,咳……”大夫无奈地摇摇头,“没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用钢板固定。”话音刚落,病人扭身就走。儿子连忙追上来:“大夫招你了还是惹你了,有病治病嘛,为啥给人家甩脸子!”母亲的眉毛拧得走了形:“八十岁的人了,还折腾啥?这把老骨头还值那个手术钱吗?”
就这样,在历经整整八十年的劳作之后,劳苦功高的右臂以如此悲凉的方式提前终结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矫月志的想法很明确:但凡能够自己对付,就尽量不去拖累子女。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再遇顶头风。转过年来,她又跌了一跤,大腿骨断成两截。至此,疲惫不堪的生命之舟完全失去动力,冰凉的土炕成了老人永久的泊位。渐渐地,床变大了,人变小了,以至于小成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婴儿。
2002年4月,一个月光皎洁的美丽夜晚,死神登门了。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回光返照的那一刻,老人已经散乱的目光又恢复了焦点,干涸的眼窝里又隐约出现了湿润的水汽。我仿佛看到,她下意识地嘬着嘴唇,执拗的目光超越了现实空间,长时间地滞留在某处,脸上的表情痴迷而又纯真,活脱脱一个吃奶的婴儿。
这是一个常人永远无法理解的神秘凝视。
她到底在看什么呢?
我猜想,这时,她或许又听见了儿时那双露着脚趾的鞋子在雨地里拍打的声音,沿着一行潮湿的脚印,她又走回了童年,又见到了生她养她的母亲。哦,母亲慈爱的笑脸是女儿一生中仅有的一段温暖记忆。当然,母女重逢的这段路程,她走得很苦、很累。是啊,这个善良的女人被自己的爱累得精疲力竭,到头来,耗尽了一生的气力。
毫无疑问,在心脏停止跳动的瞬间,她的生命之舟也自此岸到达了彼岸。据说,那个叫作天堂的地方没有烦恼,因此,她终于可以放下心中的牵挂了。
诗人说,一滴水珠可以映出太阳的明澈光辉。我觉得,一位乳娘可以映衬中国农民的敦厚身影。
哦,默默奉献的中国农民,厚德载物的皇天后土!
从某种意义上说,矫月志们就是共和国的乳娘!战争年代,他们用乳汁哺育了革命,用鲜血甚至生命为胜利壮行;新中国成立后,又继续支援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多少年来,无论再苦再难,他们都始终用一颗纯朴的爱心去理解政府、支持政府,如果没有这种无怨无悔的精神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绝无可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语重心长地说:“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鉴于本节的写作,我先后采访了老人的女儿田瑞玲和儿子田瑞夫。在逐渐深入的交流中,母亲的故事让我看到了活着的历史,儿女的心性让我看到了活着的传统。采访结束时,我特意向女儿瑞玲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如果你的女儿遇到姥姥当年的情况,你是否会支持她像姥姥一样去抚养共产党的孩子?”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支持,我肯定支持。”
我的心陡然一热,多么善良的后人啊!“丹心终不改,白发为谁新?”
这是国家的福分,也是民族的福分。

(扫码听书)
(节选自唐明华《乳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