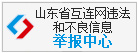第五章 今生不了情
(小序)
1962年初春的一天,崖子镇申家村的于忠英突然接到烟台地委的来信,告知近期将组织一次乳娘与乳儿的亲情团聚,并邀请她到时前来认亲。惊喜之际,于忠英一头撞上回忆的蛛网,一条条在昨天的斜阳下泛着光亮的丝线乱七八糟地扑到脸上、脖子上,黏糊糊,凉丝丝的。
1942年夏天,于忠英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女儿不幸夭折。在村支书的介绍下,她领养了刚出生不久的八路军的女儿。夫妇俩舐犊情深,把孩子视为己出。在他们无微不至的呵护下,这个名叫“光”的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
三岁那年,组织上派人来接小光。孩子又哭又闹,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养母。于忠英强忍泪水对孩子说:“光啊,听妈的话,你到阿姨那里去玩一会儿,妈忙完地里的活就去接你。”其实,于忠英心里很清楚,今日一别,相见无期啊!
孩子一走,于忠英变了个人似的,目光在虚空里飘来飘去,像孤鸟找不到落脚的树枝。每当屋外传来孩子的声音,她总是忙不迭地跑出去,看看是不是小光回来了。就这样,她变成了一个特殊病人,只有从思念的围城中逃出来,她的精神疾患才能治愈。丈夫心疼妻子,千方百计打听小光的下落,但始终没有获得确切消息。正由于此,手捧来信那一刻,喜悦的泉水从于忠英心底呼啸而出,转瞬间,就把眼角干涸已久的沟壑涨满了。
开会那天,夫妇俩早早来到现场。
活动一开始,他俩就从众多的孩子中间一眼认出了依偎在亲生父母身边的小光。分别十二载,昔日的小丫头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当主持人介绍小光的情况时,丈夫正欲起身相认,没想到,衣袖却被妻子拽住了。丈夫不解其意,于忠英朝旁边努努嘴,站起身,悄悄离开现场。丈夫跟过来,小声询问缘由,于忠英幽幽地叹了口气:“小光长得这么好,我看一眼就放心了,咱们就别给人家添麻烦了。”
夫妇俩戚然离去,一路洒泪而归。
青丝一缕系相思
发源于马石山南麓垛鱼顶的乳山河,先自南向北再自北向南蜿蜒入海,全长六十五公里,流经乳山市大部分区域。古语云,上善若水。得其涵养,上游北岸的岑岭显出一种别样的温驯。透过车窗,我看见前方的山峦如同慈祥的母亲,张开双臂把东凤凰崖村深情地拥进怀里。据史料记载,上世纪初的东凤凰崖只有一百多户人家,别看村子不大,却具有令人钦敬的革命传统。早在1932年,地下党就开始在村里活动;1938年1月,该村正式建立党支部;是年春天,胶东第一个村级妇女抗日救国会又光荣诞生;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参军或当民兵,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多达二十五名。群众基础深厚如斯,难怪胶东育儿所当年择定新址时对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村情有独钟。
车至村东头的小广场,日头刚刚偏西。午后的阳光犹如画家笔下的泼墨,给错杂的房舍涂上一层亮汪汪的暖晖。村子很静,鸡不叫,狗不咬,安详的氛围中滞留着晕乎乎的睡意。和七十多年前那些烽火弥天的日子相比,眼前的静谧实在显得太奢侈了。
东凤凰崖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自然村落。现有居民297户786 人,日常劳作主要以农耕种植和林果业为主。历经岁月沧桑,村舍格局基本保持原貌,大部分老宅现在已经翻新。循着一条悠长的窄巷,我神情肃穆地走向一个故事。我在心里呢喃着她的名字:沙春梅,一遍又一遍。她的名字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已经很熟悉。但是,先前的感受远不如现在这样深刻,真的,当我走进老宅,我才真正地走近她、理解她、敬仰她!

乳娘沙春梅的宅院
沙春梅家的宅院伫立在清冷的阳光里,三十一年前,因为儿子结婚,老屋翻盖,青石起基,白灰抹墙,唯有黑苍苍的房瓦原封未动,看上去,颜色黯沉,一如晚年的乳娘,神情忧郁,心事重重。

沙春梅夫妇
二儿媳史永绍接待了我们,她说,丈夫去地里干活,她一个人在家留守。看上去,她六十岁左右,性格开朗,干净麻利。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稠密的话语便如汩汩流水奔涌而出,于是,往事浪花般涌过来,渐渐地,我脑海中那个模糊的形象变得清晰了。
沙春梅是崖子镇下沙家村人,家中兄妹九人,排行老六。由于三哥和四姐都是共产党员,平日里耳濡目染,点滴浸润,为其日后的人生抉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二十四岁那年,明媒正娶的新媳妇拐着一双小脚走进了东凤凰崖村普通农民杨锡斌的院门。头胎是个男孩,没保住。转过年来,一个女娃又伴着嘤嘤啼哭降生了。可叹还未满月,病魔来袭,娇嫩的花骨朵儿眼睁睁地枯萎、凋零。沙春梅泣下沾襟,悲不自禁。然而,丧子之痛刚刚消弭,一个“咿咿呀呀”的婴儿突然闯进小院,把刚刚恢复的平静生活搅乱了。
原来,此前数日,村干部一直在为八路军某部杨政委的女儿寻找一位尚能哺乳的养母。据说,杨政委曾特意叮嘱村干部,希望能找个心眼好、讲卫生的。支书的目光在村里绕来绕去,最后,在沙春梅的身上定住了。口风一露,夫妇俩十分爽快,即刻应承。当三个月大的小春莲贪婪地吮吸乳汁时,那个小小襁褓已然成为沙春梅生命纪年的特殊刻度。
接下来,小丫头是用哭声同这个陌生院落进行交流的。声音孱弱却很悲恸,仿佛初涉人世便遭遇了天大的委屈。是啊,母爱缺失,情感的天幕坍塌一角,可乳娘就是补天的女娲呀!没错,此时的沙春梅就像一只痴情的春蚕,竭尽全力吐出爱的情丝,仔细包裹怀里的宝贝疙瘩。眼瞅着,小丫头越来越招人疼爱了,苹果一样的小脸蛋,一笑就旋出一对小酒窝,亮晶晶的大眼睛星星似的眨呀眨,眨得沙春梅心头像抹了蜜,黏黏的,甜甜的。
春莲两岁那年,沙春梅生了一个女儿,乳名翠芝。老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那么,叫作翠芝的小姑娘对此有何感受呢?待到采访时,昨天的故事早已白发苍苍,而白发苍苍的翠芝却清晰地记得故事里的相关细节。她说:“那时候,家里生活很困难,但凡有点好吃的,小春莲都是头份儿。我记得,小春莲最喜欢吃饺子,我妈和我奶奶就到山上挖野菜,吃粗粮,尽可能地省下细粮给她包饺子。每次只包一小碗,下锅前,我妈总是让奶奶把我领出去玩,那时候我小呀,也不知道是咋回事,等回到家,饺子也吃完了。有时候,奶奶用铁勺炒个鸡蛋,或者烙张小饼,当着我的面塞给春莲,我就那么眼巴巴地瞅着,哎呀,真是馋坏了。”
1946年秋天,春莲生母随部队路过东凤凰崖。看到女儿马驹儿一般撒欢,顿生怜爱,打算顺便领走。沙春梅趁孩子睡着的时候把她抱到前街上,两人刚一倒手,春莲醒了,扯着嗓子哭起来:“妈妈……妈妈……”生母无计可施又不甘放弃,一直磨叽到部队开拔,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半年后,上级号召参军支前,丈夫杨锡斌挥别妻儿,毅然加入解放大军的行列。谁知,军装还未上身,就在沙河之战中挂了花:一颗子弹径直贯通右腿膝下,生生掳走拳头大小一块筋肉。战斗结束没几天,这个不走运的新兵就拄着双拐,像个刚刚学步的孩童踉踉跄跄地回来了。哎呀,怎么变成这样了?右腿僵直得像一条木棍儿,而且,还短了一截!为了求得平衡,他的左腿不得不尽可能地向外撇,结果,两条腿叉成一只颠来倒去的圆规,右边的胳膊也舞蹈般扬上扬下。
在女儿翠芝的记忆中,春莲是六岁时被接走的。分别那天,沙春梅和婆婆泪如雨下,小春莲又撕又打,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我不走,我不走呀!我不要外面的妈妈!”急了,一把揪住养母的头发不肯撒手,结果,愣是拽掉一缕头发。唉,人间最苦伤别离。当小春莲的身影在远方的地平线消失后,整个世界已然变得空空荡荡了。
思念是必然的。
久而久之,思念变成一座围城,沙春梅被结结实实困在城里。实际上,思念不仅是个名词,也是个动词。尽管思念的旅途关山迢递,然而,她却觉得,那个离得最远的孩子离得最近,仿佛就在眼前,触手可及。于是,在无尽的思念中,那双颤巍巍的小脚走过数十年的漫长岁月,走过阴晴雨雪,走过千山万水。
思念之苦也让当婆婆的备受煎熬,老人时常以泪洗面,久而久之,竟然把耳朵哭聋了。
丈夫杨锡斌虽然没像妻子那样哭鼻子抹眼泪,但父女之情同样刻骨铭心。上了年纪后,他出现了明显的痴呆症状。平日里,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儿。间或,会茫然地望着家人,目光空洞而又凝滞。家人知道,他有满肚子的话要说,这些话他生生攒了一辈子。到头来,想要倾诉时,那张内秀的嘴巴却无论如何也不听使唤了。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九十六岁那年,记者前来采访,他连老伴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但一提小春莲,老人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咳,这个小丫头真招人稀罕……我打外头一回来,她就挓挲着小手朝我喊,让我抱抱,抱抱呢。”
我问儿媳史永绍:“这么多年,春莲一点消息都没有吗?”她说:“听别人讲,抗战胜利后,他们回了四川老家。春莲上学后还托人捎来几封信,再后来,什么联系也没有了。”
时光如水,从岁月的河床上潺潺流过。慢慢地,乳娘老了。
四十多年的思念之旅,她累得心力交瘁,待到挣扎着走进1989年的盛夏时,身体能量已近衰竭。“那天,她扬着手朝我嚷嚷,老二家的,我听见春莲在街上说话,你快出去看看,是不是她回来了。” 史永绍说,“我出了门,左看右看,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回到屋里,我说,妈,你听错了。她愣怔了一会儿,对我说,厢房里有个小纸箱,里边有本书,你去拿给我。真没想到,那本书里夹了一缕头发,还夹了一根丝线,婆婆拿着头发就哭上了。我不明白是咋回事儿,就问她,妈,你哭什么?婆婆伤心地说,哎呀,这个小春莲,诓了我一辈子,到临死也不来看看我……第二天中午,她就走了。”
下葬前,儿媳史永绍小心翼翼地把那缕头发放进婆婆的骨灰盒。一朝别过,便为永诀,就让这个特殊的信物贴身陪伴老人家吧。
采访结束时,夕阳已经慵懒地卧在西边的山脊上,橘黄色的晚霞墨晕般四下洇开,慢慢地,颜色变红了,变重了,温婉的光线沐浴着整个村庄,爽爽一片都是暖色。史永绍真诚地挽留道:“都这个点了,吃了晚饭再走吧。”我再三婉谢,而后,抽身就走。她愣了一下,慌忙送客。刚出院门,忽然想起什么,说:“唐作家,你等一下。”我不解其意:“还有别的事吗?”“你稍等等,我回去拿点花生,你带着。”“不用了,真的。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谢谢!”我连连摆手,一扭身,脚下的频率加快了。她带着遗憾的神情追上来,边走边用透着歉意的口吻说:“大老远的来一趟,饭也不吃,就这么空着手走了,哎呀……”我忽然有些感动,多么淳朴、真挚的情感表露啊!从儿媳妇的身上,我看到了活脱脱的沙春梅当年的影子。我想,面对真情永驻的父老乡亲,作为后来人,我们应当如何报答呢?

(扫码听书)
(节选自唐明华《乳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