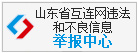回忆难忘革命岁月
于洲

1945年8月,于洲任威海卫市第一任市长。
在失败和挫折中找到中国共产党
我于1904年出生在山东省海阳县司马庄区兴善村(现乳山市乳山寨镇李家兴村)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小时候读过五六年私塾。14岁那年,地主豪绅残酷的压榨剥削逼得我家倾家荡产,我不得已跟随一位远房亲戚到东北谋生。先在鸭绿江上拉纤打杂,后又给作坊拉车填土,再后来才经人介绍到安东文信书局当学徒。学徒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其中读得最多的就是《申报》副刊《自由谈》专栏里的一些文章,其民主主义倾向对我影响挺大。后来,我到了大连,在一个书社里买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七十二烈士手札》等书籍,便在夜间偷偷地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当时颇有精神振奋、耳目一新的感觉。我很快成了孙中山先生民族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拥护者,下决心要回到山东老家干革命。
1926年初,我回到海阳老家,在乡亲中谈穷人受苦受难的根源,讲穷人应该组织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污吏、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道理。穷苦的农民逐渐聚集到我的周围,我就同他们商量办起了农民夜校。开始,入学的人数很少,后来逐渐增加到20多人,我在教他们识字的同时,讲解革命道理。看到他们对革命开始有所认识,我便从中挑选了一部分人秘密组织起农民协会,把这些人作为农会的骨干,通过他们在本村或外村暗中发展会员。
驾马沟村的国民党员于寿堂,听说我手里有《三民主义》等进步书籍,特意找我借阅。我们俩一见如故,就着当时的时局和革命任务热烈谈论起来,一致认为应该迅速把当地深受压迫而又如同一盘散沙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革命,争取自身权利,支援南方的革命战争。在他的动员下,我参加了国民党。我们一起领导发展农民协会,农会在海阳县东乡迅速发展起来。于寿堂同志后来脱离了国民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1926年冬天起,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海阳县的农民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分昼夜地投入到农民协会的工作中,每天不是被这个村请去做报告,就是被那个村请去建立农会组织。群众见我们忙得把地里的庄稼活都撂了,就自发地帮我们耕地播种,这使得我们更加没日没夜地投身到群众工作中去。到1927年春天,农民协会组织已由司马庄区普及到夏村和海阳所两个区,在其他邻近的区里也有所发展,拥有的会员多达万人。
1927年3月21日,上海的工人成功地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我们很受鼓舞,决定组织农民协会的会员起义响应。经过紧张的准备,我们于1927年6月17日凌晨把全体农会会员集合到驾马沟村,宣布武装起义。
起义的队伍分成两路,一路由我和于寿堂率领,一路由张乃晨率领。
张乃晨率领的一路,挑选了一批会武术的会员直奔南西屋村,逮捕反动区长陈锡周。陈锡周是南西屋村的土豪劣绅,清末中过秀才,擅长舞文弄墨,平素在乡里常借写状子搬弄是非,从中渔利;当上司马庄区的区长后,更是凭借职权鱼肉百姓。前阶段看到我们办农会,曾派人去海阳县政府引来便衣警察搜捕我和于寿堂同志,被我们躲过,因此,会员和普通群众都对陈锡周恨之入骨。张乃晨等赶到南西屋,趁着黑夜翻过高墙,把陈锡周从睡梦中揪起来,拖到于家庄西泊草地上,由于其民愤极大,结果没等到天亮开公审大会,就被怒火难抑的群众你一拳我一脚地给打死了。
我和于寿堂率领的一路,号称“革命便衣队”,当天夜行50里,于拂晓时赶到海阳所,区公所的乡丁做着梦就当了俘虏,我们缴获了4支钢枪和1支手枪。会员们在街头上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天亮后,我们在村头的场院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动员贫苦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争取自身生存的权利。会后,队伍开赴夏村,海阳所村有不少群众加入了前进的行列。在夏村,我们又收缴了8支钢枪。第二天,队伍来到司马庄区的乳山寨村,参加的人更多了。这时,去海阳县城打探消息的会员回来报告说,海阳城里的县长吓跑了。我和于寿堂等同志商量,决定抓住时机向海阳城进军。当时,天下着蒙蒙细雨,队伍赶到城东关时,城门已经关闭,城上的军警见队伍开来,连忙开枪射击,人们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雨也下大了,我们只好撤回岠嵎山区,从长计议。
在岠嵎院,我们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让各村的会员回去加紧做好进攻县城的准备,留下部分有活动能力的骨干到周围的区联络力量,同时保持同各村农会的联系。
到了阴历五月底,我们已经联络好了海阳所沿海的渔民和牟平一带的群众参加起义,还争取在海阳县郭城区活动的号称“革命别动队”的土匪武装赵辅臣部参加,我们直接领导的各村的农会组织也都进行了较充分的准备。于是,我们决定再次攻打海阳县城。
出发那天,天气晴朗。按照预定方案,牟平来的队伍占领城东的消气塂,我和海阳所区沿海的渔民领袖宋作梧带领农会会员和渔民群众攻占县城后面的望石山,赵辅臣领着他的土匪队伍攻城西。
我和宋作梧带着队伍从东北方向向望石山逼近,当队伍行进到山脚时,城头的敌人开了火,火力很猛烈,但因距离较远,队伍中并无伤亡。我和宋作梧领头冲上望石山,赶跑了敌人设在山上的岗哨,组织大家搬运石头构筑工事,居高临下地用步枪向城头的军警射击,等待全面攻城的时机。
我们占领了望石山的消息很快传到四面八方,各地的群众蜂拥而来,有的运来海防古炮,有的搬来抬杆枪,有的带来大刀长矛,有的抬来热气腾腾的饭菜。大家都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解放这座被贪官污吏盘踞多年的古城。但是,因为赵辅臣按兵不动,又因为用来轰塌城墙的海防古炮爆炸了,所以两天过去了,县城还是没有攻下。
第三天下午,我和宋作梧等正在望石山上研究敦促赵辅臣践约,准备夜间全面攻城,忽然得知牟平的队伍硬要撤走,挽留已不可能。我连忙赶到消气塂,部署人员接替牟平队伍继续监视城里的动向,防止敌人从东面迂回包围望石山。临近黄昏,突然听到望石山上枪声大作,大家要我快去看个究竟。我心急如焚地赶到望石山,队伍已经不见了,我连忙向北追去。天黑后,我走进一个村子打听队伍的去向,众说纷纭,无确凿消息,我只好在这个村里住下来。第二天清晨,听到房东在与人议论,说是县城戒严,4个城门挂了4个人头。我一听同志中有牺牲的,顿觉撕心裂肺般地难受,觉得倒不如自己死了好。回到岠嵎院后,我才弄清了望石山上发生的情况,原来在我们攻城时,县府和城里的豪绅用一万元钱收买了赵辅臣,并答应事后让他当警察局长,赵辅臣见钱眼开,便公然掉转枪口,伙同军警一起攻打望石山,山上的同志见敌人来势凶猛,只好分散撤回。
两天后,敌人到司马庄区来搜捕农会负责人,他们避开大路,专拣山间小路走,妄图搞突然袭击。当他们接近驾马沟村时,见山上设有武装岗哨,便连忙缩了回去,路过圈港和司马庄村时,放火烧了几处房子,抢掠了一批东西。为了防止敌人再来报复,我们组织各村农会建立武装组织,制备大刀长矛、土枪土炮等武器,学习武术,站岗放哨。我们还在岠嵎院举办了青年和小学教员学习班,加强对各村农民的革命教育。当时,全国的局势很乱,县城里的敌人自己的前途尚且未卜,就更没有心思再来司马庄区捣乱了,因此,攻打海阳城后的一段时间,农民协会在司马庄区的影响更大了,就连一些小豪绅也纠缠着央求入农会,并主动捐款为农会制备武器。兴善院的地主和尚,害怕被群众揪出来游街,主动缴出土地兴办学校,革命的气氛在司马庄区越来越浓,有的村宣传妇女剪发、放足,有的村则拆庙拖神,破除迷信,赤家口村甚至列出了名单,准备平分地主、富户的土地。
及至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蔓延到海阳境内,地主豪绅便勾结当地的封建迷信组织“大刀会”“白旗会”等向农民协会反扑过来。他们在各村野蛮地进行打、砸、抢,强迫农民协会的会员退出农会参加他们的迷信组织,对农民协会的骨干和负责人则进行疯狂的报复。
1928年2月,反动的“大刀会”在赤家口南山,一次就杀害了耿文华等13位农会的同志。一时间,封建反动势力的气焰甚嚣尘上,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就这样被断送了。我在家乡不能立足,便于1928年的春天转移到海阳西乡的辛庄头、石马滩头、夏泽、发城一带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几经反复,1929年初,海阳城里挂出了“海阳县国民党整理委员会”的牌子,国民党取代了地方军阀的统治,我回到司马庄区,被群众推举为保卫团副团长(团长是个失业穷困的旧警官)。这时,尽管我的生活安定下来了,但我的心情却异常的沉重,眼看着国民党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我看不到中国的出路在哪里,陷入了彷徨、苦闷中。
1930年冬天,经人介绍,郑天九同志(日照县山字河村人,中学毕业后曾在叶挺将军率领的铁军中参加过北伐战争)从济南来到司马庄区保卫团任政治教员。我们俩一见如故,很快就发展到无话不谈。郑天九同志告诉我,国民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豪绅利益的反动组织,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彻底进行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才能救中国。我听了这些革命道理,心里觉得豁然开朗,暗暗下定决心要找到共产党。等我们俩的关系更加密切后,我向郑天九同志表示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坚决革命到底。郑天九同志听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他就是共产党员。在失败、挫折、彷徨、苦闷中,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就像无依无靠的孩子突然找到了妈妈,那种喜悦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1930年冬,郑天九(左)和于洲(右)合影。
1931年1月,郑天九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我开始了一种完全崭新的生活。
跟着共产党百折不挠干革命
1931年4月间,郑天九同志因工作需要离开了海阳,而当时海阳的阶级斗争已日趋尖锐,我痛感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都太低了,无法适应斗争的需要,于是决心想办法去外地学习。我把自己的想法写信报告了郑天九同志,他回信表示同意,并介绍我到北平第十七中学去找一位姓王的同志接关系。
1931年冬天,我辞去了司马庄区保卫团副团长的职务,来到北平,可是那位王同志已离开了十七中,我只好设法住下来,搜集材料自学。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马恩列斯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书籍,我明白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道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胜利的学说,更加坚定了我的革命意志和取得革命胜利的信心。

1931年在北平弘达中学学习的于洲。
1932年冬,郑天九同志在日照暴动失败后来到了北平,他在听完我的学习情况汇报后表示,希望我到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去锻炼。恰在这时,担任牟海县委书记的王心一同志被捕后逃出来,也来到了北平,由他写信介绍,我立即动身返回海阳。
1932年年底,我由北平回到了家乡,接上组织关系后,便在司马庄区着手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发展了孙书堂、于天彬、孙书科、单伯苓等,又由他们在盘古庄、乳山寨、于家庄等村发展。当时,我寄居在乳山寨村一个亲戚家里,随着工作的逐渐展开,来往接头的同志越来越多,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于是就同孙书堂等同志商量,把兴善院附近的一处荒山开垦成了果园,以推广栽培果树的名义,掩护来往同志的活动。这个果园,远离村庄,环境幽静,的确是进行地下工作的好处所,很快成了革命同志的联络站。建国后,这个果园被济南军区后勤部扩建为“新华果场”,成为军区的一个水果基地。

于洲在曾经参与修建的长江大桥上。
1933年5月,组织调我到文登乡师工作,公开身份是乡师事务处科员。当时的文登乡师,师生中的共产党员有30多名,校长于云亭也是共产党员,就连不是共产党员的师生,课余在宿舍里促膝谈心的时候,或在校园里散步的时候,大家谈论的主要话题,也多半是国家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因此,这所学校,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而实际上是我们党的一个红色堡垒。我到校后,胶东特委委员刘经三同志指定我以公开身份做掩护,负责胶东特委与北方局来往秘密信件的化学处理和转递工作。
1934年初春的一天,文登县警察局长突然带着大批警察闯进学校,逮捕了校长于云亭同志和另外几位教师党员。原来是一个学生党员叛变了,向敌人出卖了于云亭等几位同志。在这样的情况下,乡师秘密党支部的负责同志继续留在学校非常危险,我便设法把支部书记刘家语(谷牧)和支部委员丛培塦同志转移到海阳县司马庄区的两所小学任教,以教学为掩护,在那一带开展党的工作。我留下来,与王炳真和张学礼同志组成了临时党支部,继续在学校里进行革命活动。坚持到秋天,环境进一步恶化,我才被迫离开学校,回到了海阳。
1935年7月的一天,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同志就组织农民暴动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已是发动全民族走向抗战的阶段,应利用山东军阀韩复榘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发动广大群众准备抗战。再从军事力量和地理环境方面看,韩复榘在山东有5个师的兵力,随时可以调到东边来镇压,而我们的暴动人员既缺少枪炮等武器,又没有受过起码的军事训练,难以与敌人正面对抗。一旦暴动后在军事上失利,我们地处半岛东端,缺少回旋的余地,因此,吸取博兴、日照等县暴动失败的教训,不宜组织大规模的农民暴动,而组织小规模的军事活动是可以的。张连珠同志和当时在场的孙学之同志点头表示赞同。后来特委还是决定进行暴动,我只有服从组织的决定。特委成立了暴动指挥部,张连珠同志任总指挥,程伦同志任副总指挥。暴动分东西两路进行:东路由张连珠和刘振民同志负责,组织文登、荣成和威海卫的群众参加,于得水同志任突击队长,进攻的重点是石岛;西路由程伦、邹青言、曹云章三位同志负责,暴动的重点是夏村,组织海阳、莱阳和牟平的群众参加。我在西路参加暴动,任务是组织第二梯队,做地下策应工作,不暴露身份,万一暴动失败,好组织群众继续坚持斗争。暴动的时间定在农历十一月一日,后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张连珠同志决定暴动推迟至农历十一月四日进行,这就是胶东革命史上著名的“一一·四”暴动。暴动失败了,胶东特委的张连珠、程伦、曹云章等主要领导人和好几十名同志壮烈牺牲了。噩耗传来,我真想带领第二梯队的同志去和敌人拼了,但我没有那样做,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够沉重了,我不能把隐蔽下来的同志再往虎口里送。这时,内线传出了敌人要对我下毒手的情报,同志们都劝我赶紧到外地去躲一躲,我也正想找到上级党组织,把暴动的情况详细汇报一下,于是再次离开了海阳县。

1944年,于洲时任东海专署副专员。
我到了青岛,想找宋竹庭同志,可一打听,宋竹庭同志已经被捕了。我又到了济南,这时,于云亭同志刚刚出狱,我便住在于云亭同志家里。原来于云亭同志在文登乡师被捕后,坚持说是坏蛋学生诬告他,文登警察局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但又不死心,就把于云亭同志押送到了济南。在济南,于云亭同志坚持在文登时的口供,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便出面把于云亭同志救了出来。于云亭同志也没有找到党组织,而我又不便在他家里久住,经人介绍,便跟着新上任的茌平县长葛栋华动身去了茌平。
在茌平,我一边在县府里做事,一边积极寻找党组织。七七事变后,聊城专区的国民党专员范筑先诚心诚意与共产党合作,率领下属各县军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恰在这紧要关头,我与在茌平县政训处做事的共产党员曹志真同志接上了关系。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发起组织青年救国会,编印《青年进步》小册子,号召青年们走上抗战前线。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组织了青年抗日先锋队,我担任队长。这期间,我们积极从青救会和青抗先中发展共产党员。
1938年春,我们与中共鲁西北特委取得了联系,经特委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茌平县工作委员会,刘昱同志任书记,曹志真同志任组织委员,我任军事委员兼统战委员。有了党的组织,同志们的抗战热情更高了,我们设法从县政府内搞出一批枪,又从八路军津浦支队孙继先同志那里领到了二三十支枪,组织成立了茌平县游击大队,马芾村同志担任大队长,我任政委。
1938年夏天,日本侵略军纠集主力,分三路进攻聊城,抗战将领范筑先誓与聊城共存亡,率领城中军民同仇敌忾,迎头痛击日本侵略者,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壮烈殉国,聊城及所辖各县相继沦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工委的同志们带领游击大队活跃在农村,凭借青纱帐,同敌伪展开了游击战。到了冬天,青纱帐落,敌人加紧了对游击队活动区的扫荡,情势非常危险。就在这艰难的时候,八路军一一五师来到鲁西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并整顿和整编了地方武装。整编后,我到了一一五师。1939年春,中共山东分局要挑选一批干部到胶东工作,我在入选之列,于是,我欣然踏上了回胶东的征途。
这时的胶东,党的组织已经健全,中共胶东特委改名为山东省胶东区党委,下设东海、北海、西海、南海四个地委。在军事建设方面,成功地举行了天福山起义,建立了人民的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后来“三军”同掖县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我回到胶东后,区党委分配我到东海地委担任地委委员兼民运部长。东海地委负责领导牟平、海阳、文登、荣成及威海卫人民的革命斗争,于克恭同志任地委书记,王台同志任组织部长,韩力同志任宣传部长,丛桂滋同志任保卫部长,职工会长是姜大同志,妇救会长是曲韶华同志。我和于克恭同志已有数年不见,今日相逢,又在一起工作,都格外高兴。
我是1939年8月到达东海区的。这时,我党在东海区尚无根据地,也没有自己的武装,地委机关基本在地下活动,当然也就没有固定的驻地了,环境十分艰苦。尽管环境艰苦,但是我们在于克恭同志的带领下,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情绪,始终都在紧张而有秩序地开展工作。到1939年年底,全东海区的各级党组织都建立健全起来,党员也发展到1000多人,通过他们的积极工作,在许多村子里成立了群众抗日组织,秘密开展抗日活动,并为转战在北海区和西海区的五支队输送了1000多名新战士。我们地委还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一支拥有150余人的队伍,编为一大队。
1939年12月中旬,胶东区党委派于得水同志率领一个营东进,试图配合东海地委在昆嵛山区建立根据地。地委机关带着新建的一大队,随于得水同志夜行晓宿,严密封锁消息,于12月20日顺利到达昆嵛山后的院下村。可是,还没等我们展开工作,顽军郑维屏、丛镜月、秦毓堂等部就联合向我们逼过来。我方力量单薄,寡不敌众,只好撤回到北海区栖霞县的郝格庄村。这次东进建立根据地的目的没有达到。
1940年春节期间,我在乳山寨的亲戚家听从青岛跑回来的人说,日本出动3万多人,从西到东对胶东进行大扫荡。我想:盘踞在东海区的大大小小的顽军司令,平日里反共、欺压老百姓时个个逞能,可要真听到日本人来扫荡,必然撂枪作鸟兽散,这正是我们发动抗日群众,拣枪组建抗日武装的好时机。于是,我连夜跑到60里外的地口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于克恭同志。于克恭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并让我立即起草地委指示,他起草建军方案。草稿拟定后,我们俩顾不上等召开地委委员会讨论,只和当时也住在地口村的地委秘书马黄汉同志一起检查了一遍,就立即动手刻印,向各县分发。各县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接到地委的指示后立即行动起来,在全区掀起了一个拣枪拉队伍的高潮。等日寇扫荡过去,顽军司令们尚惊魂未定之际,我们已在全区建立起了一支1000余人的抗日武装。
1940年3月8日,东海地委在文登县李仙庄宣布正式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九军”,于克恭同志兼任司令员。这次拣枪拉队伍的行动,被称作东海地区的“二次起义”。为了加强“九军”的战斗力,胶东区党委派于已心等同志带着北海独立二营于3月下旬赶来东海与九军会合,于已心同志任“九军”的参谋长,九军迅速成为一支令东海的顽军司令们望而生畏的人民武装。此后,东海地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过去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大小司令全盘统治,变成了敌、顽、我的三角斗争。在这种三角斗争中,敌顽逐渐合流,我军须前头拒“狼”,后头打“狗”,有时一天要经历两三次战斗。然而,又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敌顽日渐失掉民心,走向灭亡,而我军日益得到群众的拥护,发展壮大,走向胜利。
1940年4月15日,在我军讨伐驻扎文登县林村的顽军王兴仁部的战斗中,于克恭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了,同志们个个悲痛万分。在这非常时期,地委召开紧急会议,推举我代理地委书记。直到7月,胶东区党委才派来了新的地委书记梁辑卿同志和司令员孙端夫同志。
1940年9月,在各县建立县级抗日民主政府的基础上,东海区专员公署成立,孙端夫同志被选举为专员,我担任参议长和党内的财委书记、群委书记。抗日政权在东海地委的领导下逐渐向敌占区扩展,在敌人的据点附近建立“两面派”政权,向敌人的据点内渗透。

于洲(前)与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主任曹漫之(后)合影。
1941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为迎合这股逆流,胶东的顽军组成了所谓的“抗八联军”,兵分三路向我东海根据地发动进攻,我军坚决进行反击,先于2月初击溃了盘踞在文登县黄龙岘的丛镜月部,接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西进,包围了丁綍庭的老巢胡八庄,将其大部围歼,丁綍庭只率小股残兵从下水道逃走。到了3月中旬,又攻下观水村,歼灭陈昱大部,3月下旬又攻克崖子,活捉匪首苗占魁。经过这次反投降斗争,东海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已大部分连成一片,部队和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了。至1944年底,我们已经扫除了日寇在我区内的48个大小据点,日寇只能龟缩在威海卫、烟台市、牟平城和石岛等几个沿海城镇了,至于大大小小的顽军司令早就被清扫得一干二净。

1945年10月,中共威海卫市委机关报《新威日报》社成立,于洲任社长。图为报社职工暨董事会全体成员合影(二排左四为于洲)。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我内蒙和东北三省。8月10日,日寇被迫发出乞降照会,当日,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要部队立即就近接受日寇投降。消息传来,根据地的军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地委和军分区(当时已设军分区,领导区内武装)立即研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地委书记梁辑卿同志、军分区司令员刘涌同志、政委仲曦东同志、副司令员于得水同志率领,解放烟台市;一路由军分区参谋长张怀忠同志、副政委张少虹同志和我率领,解放威海卫。
我们这一路,带着军分区的一个营和三个县大队,于8月15日拂晓前到达威海卫郊区,首先占领西、南两面的高山,居高临下,对市区严加封锁;接着派出侦察员,在当地武工队员的配合下逼近市区,侦察敌情,保护我方代表进城送交促降通牒。敌人困兽犹斗,一面坚守着要道碉堡,一面派水上飞机轮番向我轰炸。天大亮后,城内的伪专员徐胡子派他的哥哥徐宝和出城接我方谈判代表进城,趁便观察我军虚实。我们觉得这是给敌人造成错觉的好机会,就故意大造声势,同时由张少虹同志对徐宝和个人晓以利害及民族大义。果然徐胡子在听了其哥哥的汇报后表示愿意投降。可是伪警备司令王述芳却下令要他的虾兵蟹将死守阵地,等待蒋匪。为了拖延时间,王述芳又特派使者打着白旗出来谈判。张少虹同志当即戳穿其阴谋,命令那个使者回去告诉王述芳,必须在36小时内缴械投降,方可既往不咎,否则罪上加罪。吓得那个家伙两腿打颤,几乎瘫倒在地,满口答应着“是!是是!”地跑了回去。

1945年10月14日,在反对美军登陆中,于洲(中方握手者)会见美军方人员。
那个所谓的使者回去之后,我们立即一边部署迫降,一边准备攻城。16日傍晚,战士们突然报告,市内数处起火。我们当即判断:敌人要逃跑。一声令下,早就做好了战斗准备的指战员闻风而动,旋风般地向市内扑去。在疾速行进的途中,我们看到海中有数十艘大小船只正向刘公岛方向移动,有的战士就端起步枪向敌船射击。这下可露出马脚了,让敌军察觉到我们不是主力,但他们已经撤出,无可挽回了。当我们占领日寇驻威头目吉山的公馆时,只见他的箱柜均未来得及搬走,可以想见其逃走时是怎样地惊慌狼狈了。
过了几天,敌舰趁夜间从刘公岛出发向市区反扑,我军早有防备,大家伏在码头上的简易工事后面,待敌舰靠近后,接二连三地把手榴弹扔上去,直炸得敌人鬼哭狼嗥,掉转船头就跑。这样持续了5个晚上之后,敌人就再也不敢来了。随后,敌伪及其家属在刘公岛上缺粮、缺水,不得不从海上逃到青岛去了。
威海卫解放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电令我担任威海卫市长,着即组织市政府。一种崭新的、更加艰巨的工作开始了。(来源:中共威海市委党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