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奔走在生死边缘 连接起生命两端
对话
“在威海,器官捐献协调员只有我自己”
李松柏是如何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的,在九年的职业生涯里他都遭遇过什么样的状况,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记者为此与其进行了对话,为大家展现这一陌生又令人尊重的职业中酸甜苦辣。

李松柏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书
记者:您是怎样从事这份工作的?
李松柏:2010年初,按照中国红十字会要求,省红十字会被列为器官捐献试点省份,我市同步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我是威海市红十字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又是学医出身,所以,按照组织要求,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当时,我参加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举办的协调员培训,系统学习了相关文件和基础知识,经过严格考核后,获得了相应资质和证书。
“在威海,器官捐献协调员只有我自己。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全国总共才两千多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记者:干这行您有顾虑吗?
李松柏:说实话,起初我也有顾虑,感觉这份工作不好做。后来我想,既然组织安排我去做,那我就全力以赴做好。时间过得真快,一晃9年过去了。
记者:您接手的第一例捐献者还记得吗?
李松柏: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2012年5月30日凌晨一点左右,那天还下着雨,这名患者已达到捐献状态。接完电话后,我冒着雨开车往烟台赶。当我见到捐献者的家属时,对方很悲伤。虽然那时我还一点经验没有,但还是按照程序顺利地做了下来。事后,捐献者家属一句话给了我莫大鼓舞:“孩子的器官可以用来救活别人,这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谢谢您帮我们完成了这个心愿。”这次成功让我更加清楚器官捐献的意义,更觉肩上责任重大。
记者:遇到捐献者家属情绪激动时,您也会控制不住吗?
李松柏:说实话,我也想掉泪。但这份工作要求我不能这么做,我只能忍着。因为,捐献者家属需要我来安抚,有些后事需要我去做。
记者:这份工作苦吗?
李松柏:怎么说呢?这种苦与大家平常所说的苦是不一样的,体现在多方面。一是要经常面对生死离别,面对捐献家庭的悲伤、痛苦和无助,我内心真实的情绪是被压抑的,时间长了,感觉很痛苦,心理压力会很大。这个压力靠别人是排解不了的,只能靠自我疏导。二是有的时候,捐献者家属因悲伤常常不吃不喝不睡,我就得陪着他们不吃不喝不睡,这个过程很累。我这个人心脏不太好,一旦感觉身体顶不住了,就赶紧拿一粒速效救心丸放在嘴里含着,然后该干嘛干嘛。三是要经常出差,很多时候是说走就走,然后在路上跟妻子说一声。另外,休假日不多。因为,从出现潜在捐献者到捐献结束处理完所有事宜,在每个捐献者身上平均要用4天左右,按照我去年完成30个捐献案例算,基本上全年无休。
记者:捐献手术整个过程,您都在场吗?
李松柏:全程在场,这是我的职责,后续的事宜也由我来负责。
记者:您最心痛的是什么?
李松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眼前逝去,尤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痛,那是捐献者家属一生都抹不平的伤痛。
记者:您最无奈的是什么?
李松柏:捐献者的器官已经进行分配了,但在捐献器官手术时才发现,器官存在病变等原因不能进行捐献。这不仅白白浪费了捐献者和家属的爱心,也让一个刚刚重燃希望的家庭再度陷入灰暗。
记者:您最感动的是什么?
李松柏:最让我感动的是,不少捐献者家属都积极投身器官捐献宣传,并与我保持着联系。他们有的会每天给我发一句早安,有的会在节日里送上祝福。
记者:您和捐献者家属关系怎样?
李松柏:我从未忘记过他们。在我的工作记录中,记录着每位捐献者的生日,每到清明或他们生日的时候,我都会发短信给捐献者家属,表示缅怀。现在,我已成为捐献者家属的情感寄托,我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亲人还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记者:如今我市器官捐献的情况怎样?
李松柏:刚开始,我带着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书一家一家医院跑,逐个科室讲解器官捐献的意义,但收效甚微。从2015年开始,威海市红十字会和卫生系统在全市二甲医院以上的ICU,神经外科设立器官捐献宣传展板,设立信息员,这让潜在捐献者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截至2018年底,我完成了42个捐献案例;仅2018年,就完成30例。如今,很多人加入到器官捐献志愿者这个队伍,我岳母就是其中一员。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正确认识器官捐献这件事,让更多的生命得以延续。
记者:如果有人想做器官捐献协调员,您想提醒他们啥?
李松柏: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要具备一定的医学教育背景和医学实践经验。因为在接触捐献者过程中,器官捐献协调员首先要初步判断,捐献者是否符合器官捐献条件,并且在和医院、患者家属沟通的过程中,也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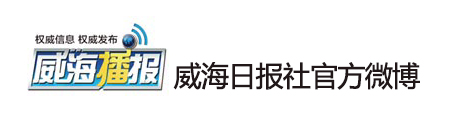 |












